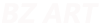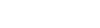新聞
2018年8月28日
在科学和艺术的临界点上 ——基于艺术史观的张芳邨BZ艺术论要 文/荣剑(著名艺术批评家) 艺术、宗教和科學,是人類精神世界的三大建構,亦是人類脫離動物世界走向文明的主要標誌。人類三萬年前棲居於洞穴時,食不果腹,衣不遮體,但藝術想像的翅膀已經展開,他們用大自然的泥土、礦物材料,混合動物脂油,在洞穴的牆壁上繪下了人類最早的藝術作品。隨著藝術的起源,是宗教的產生,人類因為現實的困苦而試圖在精神上實現一種超越,即對有限生命進入一種時間無限的想像之中。在藝術和宗教的前驅之後,科學姍姍來遲,從古希臘時代到伽利略時代,科學始終是在力求擺脫藝術和宗教的羈絆,並因為自身的進步而在改變藝術和宗教。印象派的藝術革命本質上是光學革命,而宗教改革則是在科學的壓力下完成。科學成了藝術和宗教變革的共同催化劑。 對於科學影響之下的藝術,美國著名的藝術批評家金・萊文在他的《後現代轉型》一書中寫道:“現代藝術是科學的,它是建立在對技術未來的堅信不移、對世界進步和客觀真理的信仰之上的。它是實驗的,創造新形式是它的重要任務。自從印象主義大膽涉足光學之後,藝術開始分享科學的方法和邏輯。出現了利用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立體派、具有工業技術效果的構成主義、未來派、風格派、包豪斯以及達達主義分子的圖解方式。甚至連運用弗洛依德的夢境世界理論的超現實主義形象和受其精神分析過程影響的抽象表現主義的行為方式,都試圖用理性的技巧來駕馭這些非理性的事物。因為,現代主義階段信奉科學的客觀性和科學發明,其藝術具有結構的條理性、夢幻的邏輯性、人物姿態和材料的合理性。它嚮往完美,要求純潔、明晰和秩序”。萊文所描述的科學融於藝術的情況,的確構成了現代主義藝術運動的一個主流,甚至在上世紀60年代以來演變成了機器和技術在藝術領域中的狂歡。一些藝術大師如勞申伯格、鮑勃・惠特曼等人,都爭先恐後地借助於各種工業技術手段來表現他們對科學的某種迷戀。這些現象表明,現代主義藝術借助於科學的巨大動力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內,製造出藝術各種新的形式或流派。 應該如何看待現代主義藝術的“科學性”?或者說,應該如何看待藝術和科學的關係?藝術史和科學史顯然都還沒有獲得共識。在西方的一些文化批評學者們看來,比如法蘭克福學派所主導的對文化工業的批判,就是著重於分析科學對藝術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他們實際認為,藝術的科學化是與啟蒙的墮落和人性的衰退聯繫在一起,由此意味著藝術是和重複、標準化、平均化、流水線、設計性、批量生產等工業化概念相關聯,科學的藝術被等同於資本主義的文化工業,用他們的話說:“所有文化工業都包含著重複的因素。文化工業獨具特色的創新,不過是不斷改進的大規模生產方式而已,這並不是製度以外的事情。這充分說明,所有消費者的興趣都是以技術而不是以內容為導向的,這些內容始終都在無休無止地重複著,不斷地腐爛掉,讓人們半信半疑。”在法蘭克福學派的視野中,文化工業就是一種普遍複製的文化,它的所有要素都是在同樣的機制下,在帖著同樣標籤的行話中生產出來,文化具有了圖式化、索引和分類的涵義,而藝術專家和審查官之間爭議,已經證明不再有審美的內在張力。整個世界內在的批判性和否定性通過文化工業的過濾而被完全消解,技術的合理性由此變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由此也就具有了社會異化於自身的強製本性。 在我看來,現代主義美學的實際進程,其實並不是像法蘭克福學派所想像的那樣,完全在一個科學的軌道上被不斷地複制出來從而走向墮落。自印象派繪畫拉開藝術的現代主義帷幕以來,現代藝術就是作為啟蒙運動所倡導的理性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和整個社會的“祛魅化”相適應,現代藝術通過塑造不同於古典藝術的視覺形象而把政治的或宗教的意識形態從藝術領域中完全驅除出去,藝術真正回到了自身。以印象派和野獸派為代表的色彩革命和以畢加索為代表的造型革命,是藝術史上前所未有的創新。因此,藝術的現代性就其想像創造的本質而言,是和科學的工藝性和復制性根本對立的。科學和工業在賦予現代藝術的某種形式時,其實並未限製藝術想像的空間,也沒有消解藝術的“原真性”。在藝術的現代主義時期,確如哈貝馬斯所概括的那樣,藝術取得了和科學同等重要的位置,成為20世紀自主的價值領域。現代藝術的自律性並沒有因為攝影和照相技術的廣泛使用而受到致命影響,在本雅明提出“複製的藝術”之後的幾十年內,現代主義藝術按其自有的邏輯在歐洲和美國迅速發展,產生了諸如德國新表現主義和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等重要藝術流派。 然而,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現代主義藝術遭遇了真正的危機。用金・萊文的話來說:“現代藝術許諾過一個玫瑰色的燦爛未來,一種無止境的風格進步。但是,在1968年左右——那個凝固汽油彈、退學和廣泛分裂充斥的時代——對現代藝術的樂觀,對技術科學的武斷信念,對純粹、邏輯、形式過程的信賴,都越來越堅持不下去了。替代無限進步和發展的是缺失和斷層,通貨膨脹和價值貶值。……在一個不單一的世界中,純粹化是不可能的,現代主義已經死了”。 在現代主義的一片廢墟之上,後現代藝術開始崛起,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便席捲歐美大地。作為對現代主義藝術的反動或超越,後現代藝術表現著和前者根本不同的美學立場,它們對“藝術作品的自律性”和“美學的自律性”的觀念加以攻擊,而這些觀念則是現代主義的哲學基石。在後現代的語境中,藝術可以是一切,但惟獨不再屬於它自己。後現代藝術之父杜尚在20世紀初就曾宣布世界上最平常的物件都可以成為藝術,他對“什麼是藝術”這個問題的經典回答是:“什麼不是藝術”?在後現代藝術中,重複和雷同不再是藝術致命的敵人,無風格成為一種風格,“拼貼”、“挪用”和“模仿”成為藝術表現的主要手法,工業標準化生產和流水化作業被大張旗鼓地引入到藝術生產過程中,藝術家的職責只是出售觀念,他可以像擁有資本的老闆那樣僱人畫畫而不再遭遇道德的譴責,公開的模仿甚至剽竊都成為時尚,由此導致了美國文化批評大師詹姆遜所描述的那種狀況:“迄今沒有任何社會像這個社會那樣標準化,人類、社會和歷史的短暫性的溪流也從來沒有如此均勻地流動”。很顯然,在後現代的歷史語境中,藝術的同質性和復制化才真正地從技術層面上升到一種觀念、一種哲學,和“複製”相聯繫的是“拼貼”、“挪用”、“戲仿”、“圖解”等新的關鍵詞,這些關鍵詞顛覆了現代主義美學久已形成的學院化和精英化的傳統,使藝術迅速下沉到大眾主義的消費浪潮中。本雅明從電影和照相中所看到的藝術的複制化,在新的圖像時代,借助於計算機和媒體的巨大效用,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藝術主流。由此就不難理解中國的當代藝術為何還在它的社會母體尚處在現代主義的襁褓期,就迫不及待地掙脫而出以完成它的後現代蛻變。在前現代的、現代的和後現代的話語並置的情景下,“複製”的話語已經赫然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主流話語,它支配或影響著中國的當代藝術生產,使得那些後現代藝術的經典視覺符號一再被重複地製造出來。 基於藝術和科學的關係所展現出來的藝術現代史和後現代史,是不是已經窮盡了藝術和科學的全部關係?現代藝術對科學所表達出來的獨立性和後現代藝術與科學的糾纏,是不是意味着艺术还需要在科学的维度下做进一步的思考?这是我在阅读和理解张芳邨BZ艺术时所涌现出来的问题意识。自印象派以來的一部藝術史,科學自始至終沒有缺場,它是以不同方式介入到藝術的創造和變遷之中,但必須指出的是,藝術家們不管是基於現代的還是後現代的立場,科學都是“間接”地介入於藝術場域,或者是作為藝術的背景出現(現代藝術),或者是作為藝術的工具出現(後現代),在這兩個不同的藝術階段,科學的機理和藝術的機理都是各自獨立存在的。由此来看张芳邨的BZ艺术,他有別於以往藝術史的意義在於,科學是“直接”出場,科學直接參與了藝術的創造,藝術家刻意突破藝術和科學的臨界點,把科學反應和藝術造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打造了一種獨特的藝術——BZ藝術。 首先,张芳邨的BZ艺术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说法,而是基於一種嚴肅的科學原理,即由前蘇聯科學家別羅索夫和柴波廷斯基在1959年共同發現的“BZ反應”(以他們名字中的第一個字母命名)。BZ反應的實質是一種化學振盪,在適當的催化劑如錳和鈰作用下,用丙二酸氧化溴化鉀,在皮氏培養器中混合溶液後,可以看到培養器中間不斷輻射出有顏色的波紋,溶液先變成藍色,接著變成紅色,然後又變成藍色,如果繼續添加物質反應將不斷進行。這個反應完全是一種化學鐘。這種反應就是所謂的自身催化,也就是說反應的生成物能夠催化反應,加快自身的合成。BZ反應表明,反饋可以做為一種提供振動的方式,非生命系統中的簡單成分可以產生自發的複雜模式和結構。张芳邨把BZ的化学反应直接运用于画布上,讓各種顏料在畫布上自身反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圖案畫面。這種畫面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更不可能產生所謂繪畫中的贗品。這是顏料的“自組織”繪畫,畫面是由顏料的自我運動而“自發”形成的,藝術賴以憑藉的物質顏料本身自然屬性的BZ反應,改變了從古到今傳統意義上的藝術觀念和表現手法,使藝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態的可能。 其次,张芳邨的BZ艺术是科学的艺术性的直接显露,科學和藝術的關聯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呈現出一種內在的聯繫。按照傳統的科學觀,科學是由邏輯和理性所建構起來的,科學所觀察到的對像很難和藝術聯繫起來,科學的“形象”無從表現。但實際上,現實中一切醜陋的事物,在顯微鏡下還原到最細小的分子或原子結構時,人們觀察到的卻是最美麗的景象。科學不僅能夠探究事物的“真相”,而且也可以呈現事物的“美相”,大自然的深層奧秘和豐富性是由無數自組織運動所構成的,BZ反應把“自然之美”真實地呈現出來,這是科學之美。科學和藝術的臨界點在BZ藝術中被打破了,我們可以把BZ藝術稱之為科學的藝術,也可以稱之為藝術的科學。 第三,BZ藝術不僅是繪畫顏料的革新和再造,是一種新的繪畫材質的運用,而且也是一種新的藝術觀念和方法的突破。顏料通過BZ反應所進行的自組織運動,在畫布、宣紙、玻璃、陶器、瓷板等載體上所形成的畫面效果,是科學反應的產物,也可以看作是自然天成的結果。材料的革新必然帶來的是藝術觀念和方法的革新,“自然”的表現改變了繪畫在傳統意義上的有意調合、製作與描摩的表現手法。從這個意義上看, BZ藝術也許是一個能夠超越由印象派所開創的色彩革命,它真正洞察到了色彩生成、變化、合成的原理和機制,使藝術真正還原到天人合一、自然生成的境界,藝術家潛意識情感的發揮、心靈的介入和觀念的主導,均以“物化”的形式由物理化學的自組織運動達到一種和諧與呈現。在這個“BZ”反應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物質顏料的自我催化,另一方面又是主體和客體的交融,最後使非生命系統中的簡單成分被演化為一種複雜的模式和結構,形成大自然和人類都難以想像的美麗壯闊的圖畫。 第四,BZ藝術是自組織的藝術,是自然天成的藝術,也是偶然的藝術,於是,人們會問,藝術家的主體地位何在?藝術家的在場是不是就如同一個科學家?手裡拿著不是畫筆而是各種瓶子?這樣的繪畫場面豈不就是徹底顛覆了傳統繪畫的作業方式?波洛克的“滴撒”式繪畫已經顛覆了傳統的架上繪畫方式,他所追求的繪畫的偶然效果現在已被藝術史公認為是他藝術成就的一個決定性因素。和波洛克比較起來,张芳邨的BZ艺术在操作的过程中,偶然性就更大了,他的作品的成功率大概只有十分之二,瓷板畫的成功率更低,是百分之幾。作品“成活率”如此之低,一方面可以視為是作品的自我生成,另一方面也可以視為是藝術家的自主選擇。在作品自我生成和藝術家自主選擇的過程中,藝術家的主體性始終是體現在觀念、情感、經驗所共同構成的藝術判斷上,他的主體介入方式是多樣的,諸如調整配方,改變試劑,增加或減少某種顏料,引導顏料流動的方向和力度,當畫面達到最佳狀態時,最終由藝術家來決定作品的完成時刻。因此,BZ藝術對藝術家來說並不是一個被動的藝術過程,它並沒有改變藝術家和作品的關係,主體和客體只有達到高度統一時,作品才會“順乎其然”地被創作出來。 我并不认为张芳邨的BZ艺术一举解决了艺术和科学关系中的全部问题,但是,他的藝術探索至少涉及到瞭如下問題是值得批評界高度關注: BZ反應讓繪畫媒介從“死”的材料變成了“活”的材料,顏料基於化學反應所進行的自組織運動有可能徹底改變以往所有繪畫的方式和方法。 基於BZ反應的繪畫是科學的藝術性的直接呈現而不是間接介入,科學反應和藝術造化具有大致相同的旨趣和境界,科學和藝術在對立中呈現統一。 BZ藝術是自然天成的藝術,是偶然的機遇的藝術,藝術家的主體性就在於把偶然的機遇的藝術效果在瞬間“定格”下來,主體和客體必須高度統一。 BZ藝術是科學反應和藝術造化的統一,是藝術和工藝、藝術和技術、藝術和科學的統一,當然,也是藝術和自然的統一。大千世界其實是一個整體。 丹托提出藝術的終結,是基於藝術的可能性已經徹底喪盡;我認為,张芳邨的BZ艺术展示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榮劍 2017.10.5 榮劍:哲學博士、著名藝術批評家、策展人。2005年創辦北京錦都藝術中心,自2006年4月起,在“第三空間”的理論主題下推出了“中國抽象藝術系列展”,迄今已舉辦了二十多回,在業界產生了良好的反響,被業界公認為是中國國內推廣抽象藝術最重要的藝術機構。榮劍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了上百萬字的理論文章,出版的专著有:《民主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超越與趨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馬克思晚年的創造性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社會批判的理論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其中《民主論》一書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被美國國會圖書館作為經典文獻收藏。
2018年8月28日
以藝術史為基礎的張方存BZ藝術的藝術與科學話語的決定性論點 作者:榮健(著名藝術評論家) 藝術, 宗教和科學是人類精神世界的三大結構, 即. 人類的主要標誌,從動物世界出發,向文明走. 三萬年前, 人類得住在洞穴, 有沒有足夠的食物和衣服, 雖然, 藝術想像的翅膀已蔓延; 他們用泥土, 礦物材料, 並混合動物油脂畫向下洞壁最早藝術作品. 隨著藝術的開始, 跟隨誕生 [...]
2018年8月28日
色彩的解密与革命 ——张芳邨“BZ艺术”解读 文/荣剑(中国著名艺术评论家) BZ反应的基本原理是由前苏联科学家别罗索夫和柴波廷斯基在1959年共同发现,並以他們名字中的第一個字母命名。 BZ反應簡稱化學鐘,是一種化學振盪。在適當的催化劑如錳和鈰作用下,用丙二酸氧化溴化鉀,在皮氏培養器中混合溶液後,可以看到培養器中間不斷輻射出有顏色的波紋,溶液先變成藍色,接著變成紅色,然後又變成藍色,如果繼續添加物質反應將不斷進行。這個反應完全是一種化學鐘。這種反應就是所謂的自身催化,也就是說反應的生成物能夠催化反應,加快自身的合成。BZ反應說明了兩個重要問題:反饋可以做為一種提供振動的方式;非生命系統中的簡單成分可以產生自發的複雜模式和結構。 BZ反應長期不被科學界所關注和重視,就像化學振盪反應的發現雖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但卻長期被單調的科學思潮所壓抑。若不是化學鐘、化學波被觀察到了,那麼也許永遠也沒有人像普朗克預計光子,泡利預言中微子那樣意識到有這麼一種奇妙的反應。 伊·普里戈金在《從混沌到有序》中指出,化學鐘、化學波向傳統化學提出了挑戰。他在對物理、化學和生物有序現象系統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種全新的理論。其理論觀點是:一個與周圍環境有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開放系統是遠離平衡的非平衡狀態,對系統進行微小的擾動,或系統自身的波動,使某個性質的變化超過一定限度,系統便可能發生突破,會由原來的無序混沌狀態變成時間、空間等方面有序的新狀況。這一理論很快受到各門學科的重視,對科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更是指出化學發展的必然趨勢——非平衡態化學。這就是“耗散結構”理論。 實際上,物質世界的一切體系,從基本粒子、原子、分子到微生物、動物、植物、人類和人類社會,不論是生命體系還是非生命體系,在由低級到高級進化和發展過程中都存在著這種自組織的共同特性。這是世界物質統一的又一佐證。能量的運動,宇宙萬物的運動,就是不平衡的表現,完全平衡的宇宙將會凝結。對生物來說,變化終結的平衡態就是死亡。 混沌論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國科學家施萊辛格所說:“20世紀的科學將永遠銘記的只有三件事,那就是相對論、量子論和混沌論”。物理學家福特也認為混沌論是20世紀科學上的第三次革命。他說:“相對論消除了關於絕對空間和時間的幻象,量子論消除了關於可控測量過程的牛頓式的夢幻,而混沌論則消除了拉普拉斯關於決定論可預測性的幻想”。化學振盪是開啟化學混沌論的一把鑰匙,BZ反應的發現使這一切的發生成為可能。普里戈金1968年提出的耗散結構理論在1997年獲得了諾貝爾獎。 BZ反應在藝術色彩、構圖、自然肌理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这或许就是张芳邨的“BZ艺术”的奥秘之所在。 紅、黃、藍是宇宙當中的三原色,人的肉眼可辨別的兩千多萬種顏色都是由三原色組成的。张芳邨把三原色稀释到适当程度(可反应的程度),注入空白畫布上色彩呈現出千變萬化、豐富多彩、奧妙無窮,構圖形式呈現出混沌無序、自然生成、無律可循,自然肌理呈現出螺旋狀海浪式有序的波紋。 這個自然生成的繪畫注定是抽象的,它排除一切主題、意念、情感的注入(這種注入總是有限的),還原了它的純粹,恢復了它的本質,展現了它的無限。偶然性是它的實現手段,內在韻律的交互達到了藝術所追求的氣韻生動,在平面上推向極致。 美國有本講科學發明史的書,在一幅阿爾塔米拉洞穴的野牛彩色插圖下作了這樣的說明:這位不知名的藝術家對色彩和動作有一種敏銳的感覺……,當人‘發現’了藝術,人也就發現了化學。把油和顏料混合後,色彩讓它在岩壁上乾透,製造了最適合使用的顏料,無疑也就是人類所實現的第一次化學作用。化學的發展確實是和藝術的發展聯繫在一起的。 张芳邨是在1997年画具象油画时发现和创造了这种BZ画法,又稱“BZ藝術”,他潛心探索研究十多年來完善這種畫法。在繪畫過程中,他把礦物質的顏料稀釋到適當的程度,讓各種顏料在畫布上自身反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圖案畫面。這種畫面是獨一無二的,不可重複的,更不可能產生所謂繪畫中的贗品。這種無意自然形成的表現手法改變了繪畫傳統意義上的有意調合、製作與描摩的表現手法,從而徹底改變了從古至今藝術表現以及形式探索的本質。藝術表現手法從古代岩洞壁畫到今天的當代藝術無不是表現事物的表像以及所謂的思想觀念,而BZ藝術探索追求的是藝術自身的本源,和藝術在物理化學特性中所呈現出的自然性。藝術賴以憑藉的物質顏料本身自然屬性的BZ反應,改變了從古到今傳統意義上的藝術觀念和表現手法,使藝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態的可能。 這個發現是一個能夠超越由印象派所開創的色彩革命,它真正洞察到了色彩生成、變化、合成的原理和機制,使藝術真正還原到天人合一、自然生成的境界,藝術家潛意識情感的發揮、心靈的介入和觀念的主導,均以“物化”的形式由物理化學的自組織運動達到一種和諧與呈現。在這個“BZ”反應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物質顏料的自我催化,另一方面又是主體和客體的交融,最後使非生命系統中的簡單成分被演化為一種複雜的模式和結構,形成大自然和人類都難以想像的美麗壯闊的圖畫。 榮劍於北京錦都藝術中心 2008年6月14日
2018年8月28日
繪畫來自銀河:论张芳邨的BZ艺术 文/夏可君(著名艺术批评家) 艺术的神秘在于记忆的唤醒,藝術的天才來自於自身生命中神秘記憶的萌發,尤其是喚醒那遙遠的宇宙記憶,霍金不是說過:最為神秘也最為讓人感動的是宇宙中那遙遠的相似性,藝術家就彷佛如同科學家,一直在尋找這可感的與不可感的相似性,只是對於藝術家,更多是通過自己的作品來與宇宙發生節律性的共感,藝術的秘密就在這裡閃爍出來。 藝術家一直在尋找這來自於宇宙相似性的隱秘共振,以自己發明的色彩與形式,釋放隱含在質料中的宇宙能量,使之獲得精神共感的形式。這就要求藝術家去尋找獨特的質料,通過獨特的運作,導致能量轉變,藝術的形式語言一旦顯現出來,就導致顏料的質量改變。這也正是當代藝術為何不斷要求突出材質本身的質料感,就是要觸動引爆其“質量改變”,通過藝術家個體的想像力,把自然材料轉化出精神的共通感受,讓材質呈現出令人心醉神迷的形式感。 艺术家张芳邨以其独特的BZ艺术给当代艺术带来了新的艺术景观与艺术奇迹:這是藝術家發現與發明了獨家的BZ顏料和溶劑,讓礦物質顏料更為水溶性與吸納性,但又更為具有火熱的質感,導致水性與火性的奇妙融合,徹底改變了材質本身的質感,而且,藝術家在畫布、宣紙、玻璃或亞克力板、瓷板或瓷器上,用特製的溶器盛上已調配好的顏料,在算好調配比例和先後步驟後,畫家也基於宇宙三原色紅、黃、藍,來達到其想要的畫面整體色調的間融感,隨後陸續添加實驗BZ藝術顏料和溶劑,導致畫面出現複雜的畫面視覺效果。而且,BZ藝術有著自身發明的繪畫能量公式:E=mntf/s除以6.25。其中,Z材料介質光度,單位:1級—7級;t代表BZ藝術繪畫反應所需要的時間,單位:(s)秒;f 代表振動頻率,單位:赫茲(Hz);S代表BZ藝術繪畫所需面積,單位:(m)平方米;6.25是BZ藝術宇宙常數k 。而且畫面一般要經過幾天的自組織運動,最終呈現藝術家渴望的BZ藝術作品。 通過這個“配方”的各種重要參數,讓我們看到了技術與藝術的完美配合。其中有著介質的“光度”——新顏料釋放出的光感超過了油畫已有的光感,更為絢爛也更為流動,這也是藝術家第一次解決了瓷板畫上顏料相溶的難度;而“時間性”——這正是中國藝術要貢獻的原理,充分讓時間起作用,是時間在做過,是時間“養化”的藝術,繪畫就是“養畫”!而振動“頻率”既是自組織運動與振動後留下的痕跡,也是振動本身就應和著自然宇宙的“節律”,也要求藝術家尋求藝術形式與宇宙節律之間的感應關係。而繪畫的“面積”則是畫面平面的空間場,顏料可以伸展的空間,在實像與虛像之間的張力關係。置於宇宙“常數”,則是充分利用宇宙已有的比率,達到材質最大的“可塑性”。如果我們回到藝術家與顏料共通運作的動作,而藝術不過是獨特的動作呈現,藝術家就是讓BZ顏料產生化學振盪反應,加入催化劑,使之更為生動多樣,導致礦物質的不同粘合與化解,通過不斷地生成與混合,以及持續的微妙振盪,形成美妙無比的紋理與痕跡。 我們就有必要思考BZ藝術的實驗與創作所帶來的獨特藝術原理。 首先,這裡有著藝術與科學的內在對話,通過化學反應與自組織的生成,來形成畫面形式語言,這是藝術語言的一種獨特生成方式與生產方式,BZ藝術把材料向著科學的元素性關係還原,把元素性向著生命質感還原,並最終在視覺的流動性與宇宙的心像之間獲得共感。 其次,藝術家的探索性還體現在不同材料上的生成,因此生成的畫面特質也不同,這是世界的多樣之美:瓷板畫上的熱度與色料開始幾乎不可能的相融(這是傳統所沒有解決的問題,被BZ顏料所改變),玻璃上的光滑與純粹度(既有著光滑的質感又有著色彩的透明度),紙上的流動融合性與細微性(這也是傳統水墨所不具備的張力,水性與火性的內在相溶),布上則更加體現微妙的色度與幽微的神秘(如同創世記系列上的純粹單色與內在的幽秘感)。 再其次,就BZ藝術與中外藝術史的關係而言,如此流動著的色彩,一方面,不同於張大千等人的潑彩,BZ藝術是利用顏料自身的震動所留下的痕跡,看起來是質料自身的自動生成,但其實有著藝術家的主體控制。另一方面,又與波洛克的滴灑繪畫不同,波洛克更為強調必然的控制,看似偶然,其實有著線條上迴旋的節奏與疊化,尤其是生命主體及其慾望的發洩與迴旋感。儘管之前藝術家畫過與波洛克的炫舞線條異常相似的作品,但線條更為細密與柔美,而一旦藝術家更為接近BZ藝術本身的材質自組織原理,就更為順著材質本身的震動而塑造畫面,更為自然化,充分利用了材質本身的可塑性(plasticity)。如此尊重材質本身的可塑性,也許是來自於中國水墨藝術的啟發,中國藝術強調順應自然的變化,尤其是水性的生成流動,此自然的可塑性,乃是中國當代藝術可能貢獻的原理,這是回到一種西方神學《創世記》的語言,一種在混沌中普遍性光感顯現的元語言,如同艺术家自己把自己的作品命名为《创世纪》所对应的! 接下来,令人驚嘆的是BZ藝術乃是一種來自於銀河的藝術。當我們純粹面對BZ藝術的畫面語言,驚訝其色彩的絢爛與豐富多變,這給繪畫帶來了無與倫比的艷麗色彩,其紅色,黃色,既有著單純性,還有著濃度,有著質感,以其火焰般的燃燒,似乎點燃了繪畫!其肌理感,似乎是繪畫燃燒後的美妙倖存物。BZ的繪畫語言,乃是一種原初語言,是對宇宙語言的本源記憶!看到那些色彩斑斕的作品,那些流動著的畫面,讓我們驚嘆,藝術再次回到了天空,似乎這是來自於銀河的繪畫!這是一種迷人的宇宙記憶。顏色如此燦爛,㶷爛,充分發揮了材質的可塑性與吸吶性,喚醒高溫的宇宙能量,讓畫面好像燃燒起來,如此熾熱,如同銀河的流層,這是銀河的繪畫,這是一種新的能量美學。BZ藝術乃是釋放能量粒子,使之改變,呈現出隱秘微粒子的痕跡,流動與呼喊的愛之痕。整個畫面的圖像,似乎萬物在開放,萬物如花,似乎還在綻放,還在湧動,傳達出藝術家的宇宙之愛。 最後,BZ藝術,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另一種藝術的可能性,這就是技術與自然的關係:它越是技術化,卻越是看似自然。這是與日本藝術的不同:後者越是自然,卻越是人為技術化,越是少,其實是更為人為地減少。中國當代藝術,卻看起來如此技術,卻在於激發自然的潛能,把西方式抽象向著自然的質料還原。 一種新藝術的出現,乃是通過生命的機緣而發現一種獨特的材料,通過獨特的技法釋放出內在的能量,並使之獲得獨特的形式,使之釋放出獨特的精神能量,此能量可以感染每一個來到作品前面的觀眾。以此打開未來的能量空間,其中有著藝術的難度,而其難度則有顯得異常自然隨機,異常美妙與豐富。 尤其是在布面上的《創世紀》系列,無疑是繪畫上的經典作品,那些顏料留在布上的流散痕跡,如此美妙,如同花跡,看似細密畫,抑或好似昆蟲世界的迷宮,萬物都在那裡隱秘地遊戲與生長,又還好似還在膨脹的宇宙,宇宙遙遠的相似性在這裡留下慷慨的痕跡,隱含著的痕跡愛意還在隱秘地漫延,是的,繪畫是供我們來呼吸的,這是宇宙所給予我們的生命糧食。 夏可君 2017.9.1 夏可君:哲學家、藝術批評家、策展人。已經出版個人著作近十部。他試圖以“餘”的哲學概念,在古今中西之間,找到中國哲學走向世界的一條新的道路。並試圖以“餘象(Infra-image)”與“虛薄藝術”(Infra mince Art)、無維度、“默化”與“虛托邦”等概念形成一系列關於中國當代藝術的系統思考,讓人中國當代藝術具有新的貢獻,重寫現代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