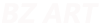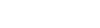新聞
2018年8月28日
話題提出者: 徐虹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学术部 主任 第十一届美术批评家年会轮值主席 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學術一部副主任。 1985年畢業於上海師範大學藝術系油畫專業。 1985—2002年在上海美術館學術部工作,從事館刊編輯、理論研究、展覽策劃和繪畫創作。 1991—1992年在中央美院美術史系助教進修班進修; 2002年到北京中國美術館工作; 曾參與策劃多次國內外藝術展覽和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和美術批評以當代中國繪畫和女性主義美術批評為主。 我們越來越回到藝術本體的討論,我覺得我們可以進入學院式的話語“何為藝術”的評判,我想我還要更回到傳統一點,畢竟我們今天是在討論藝術問題,而不是討論科學問題,從報紙上,包括電台,關於科學的普及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在這裡再討論的時候就跟大眾討論科學一樣,沒有什麼太大的奇妙之處。 社會發展到每一階段,必然是藝術家技術和藝術之間關係非常密切,使我想到早期的人類繪畫都是畫在洞窟和牆壁上的,等到建築開始要減輕承重,創造了玻璃,玻璃的黑框子裡開始有繪畫的構圖以後,加上宗教的需要,人們開始在《聖經》和木板上可以隨時帶著宗教的圖像來進行祈禱,進行宗教生活,所以單色繪畫就出現了。 所以繪畫和科學在很大意義上,不僅僅是思想,我覺得更多的是在技術的發展和關係上。在中國人畫抽像畫,特別是他的作品的意義,使我們想到的是中國人畫抽像畫怎麼畫?在西方的抽像畫,我們從波洛克以來,大量的熱抽象和冷抽象,我們都知道他們一個是從自然中抽像出一些形體平面畫,另外是表現感情的激情來體現畫面的流動感,一個是非常理性地劃分空間,一個是非常激動地潑灑顏料造成畫面的激情澎湃,使參觀繪畫的觀眾從中感受到藝術家的感情,因為感情是看不到摸不著的,除非他發脾氣、在那裡吵架。一般來說,在繪畫上出現的感情,確實要通過畫面的結構、色彩、線條、畫面流動的方向,以及畫面筆觸的粗細、厚薄等等來去除形象,而純粹感覺到情感的質感。 中國沒有辦法從視覺形象脫離,哪怕是從書法去畫抽象,也是要藉助書法的字的形象,所以對中國人來說,畫抽象非常難,就像吳冠中來說,斷不了這個線。张芳邨的艺术我觉得最大的意义还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搞抽象的可能性,他可以去掉他在地球上看到的生長的物體的那種畫像,可以看到的去掉這種形象,他總算可以自由地,可以在宇宙天空裡遨遊,可以去畫一種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終結,既沒有生也沒有死,既沒有一個故事情節也沒有一種情緒的特別要讓人感覺到的高興和悲傷的這麼一些內容。中國人能不能離開這些敘事內容,张芳邨这些绘画还是在这方面告诉了我们一些内容。 比如说如果要把张芳邨的绘画完全用科学或者科学艺术结合,完全用化學反應來說,價值不是很大。為什麼價值不是很大?因為現在任何更有名的藝術家,要想參加今年的科學與藝術,在清華博物館的第四屆,就是用影像來做,影像做的宏觀物理的交融,光的流感,這個效果實在讓人太震驚了,在整個黑房子裡是一個非常大的屏幕,讓人看到宇宙空間,進入各個屋子之間的撞擊,給人的震撼和感覺,物理和科學的反應更是震撼,在平面上一個小的,讓你想像進入到一個宇宙空間,這個直接了,國外許多影像作品已經在反映這方面的內容,而且用影像來反映,有時候也是要一點點畫出來的,有些也是要用暗黃色,通過各種手段來做,可能就是這種方法更多,物質更多,手段更多,影像更光滑,時間感和速度感更合適。 所以完全用現代科技技術來和現代科技的發現混在一起,至少從視覺上和心靈上的反應,這個我覺得從這方面來說,藝術與科學的方法來做,反而更信服。 背景來說,還是要回到學院派的批評上去,還是要看你的結果,還是要看你畫面中最後告訴我們的形象和給我們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因為人的興趣是自己對自己的興趣,如果沒有人,就算怎麼變化,就是因為人,才開始要考慮我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要考慮到終極命運,要考慮到宇宙和我的關係,所以最後還是要回到人。所以我覺得在這裡我還是要回到我的基本形式判斷上。 第二是你在結構上脫離了時間感,我說脫離了時間感就是沒有開始和沒有終結的時間感。如果作為我們一般的敘事,一般的社會敘事,一般的說一朵花、一個太陽,或者說一個我們所認知的社會現象,因為人給世界立了法則,給自然萬物規定了這個秩序,我們怎麼出生,怎麼死,所以從你的作品裡面,從西方抽象繪畫裡發展出了一種沒有時間、沒有啟示的概念,雖然這個概念是科學、物理學的,但是人是用另外一種方法怎麼來解釋世界。 第三是在形式構圖上,你的色彩完全和傳統繪畫色彩相比,冷暖關係可以不顧,但是在整個畫面上強調節奏,互相之間的關聯上,你還是仿造了想像和自然結合的方法。 我為什麼說想像,第一,你想像宇宙的物質之間的溶化是怎麼樣。第二,你從自然中,或者從陶藝的釉的變化,從窯變裡面還是找到了很多可以獲取的形象。第三,你這篇灰的畫裡面,因為沒有時間感,所以你在這個灰的畫裡是沒有方向感的,既不想出來也不想進去。 再就是你(张芳邨)和西方抽象绘画、同波洛克最大的區別,反而有中國的道教思想,有一種飄浮在大千世界自由自在漂到哪裡是哪裡的東西,我反而覺得有東方的思維意識在裡面,有一種非常慢的,浮現在在外面的,非常自由的、生活的量子、生命的波動,讓它自由振動的感覺。所以我覺得你的繪畫與其我們更多地談科學,還不如說在科學影響下,我們怎麼再來理解傳統的東方思維,怎麼用科技方法來表現我們對這種思維的形式上的顯現。這樣的話,我覺得你對中國繪畫的貢獻大於你對科學的貢獻,對繪畫思想在現代物理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下你所解釋的一切和生命有關係。
2018年8月28日
話題提出者: 杨卫 湖南益阳人。先後畢業於湖南工藝美術職業學院與吉林藝術學院,1991年開始工作生活於北京,為較早一批職業藝術家。曾作為“艷俗藝術”的代表藝術家活躍在上世紀90年代,2000年後轉入藝術批評與策劃。2002年參與籌建北京犀銳文化藝術中心,擔任該中心主持。2003年被中國藝術研究院特聘,參與創刊《藝術評論》雜誌,擔任首席編輯。2006年至2009年擔任宋莊藝術促進會藝術總監。現為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秘書長,國際藝術評論家協會(AICA)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策展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學術委員,中華國際科學交流基金會科學與藝術委員會委員,北京湘籍藝術家聯誼會會長,天津美術學院客座教授,吉林藝術學院客座教授、碩士生導師。 张芳邨的作品触及到很多,尤其觸及到我們不擅長的科學。作為一個個案,张芳邨先生做得非常充分,因為他的作品涉及到我們美術界過去很少談論的問題,所以他做得非常充分。 《愛之痕》這本書我以為是一本畫冊,打開原來是一本書,書裡涉及很多內容,包括他自己的成長歷史,包括對藝術史的梳理,包括對科學的豐富等等,也就是說他提供了一個途徑讓我們走近他。 這樣一個藝術家,我始終覺得他還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現象,並不在我們的藝術潮流當中,他在一個跟隨的藝術脈絡而成長,但是又另闢蹊徑的一個藝術家。他很知道自己的位置,也很知道如何讓我們去了解他、走近他。這點,张芳邨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做了大量的準備,知道自己如何在藝術史或者在藝術格局裡面把自己放在什麼位置,甚至某種意義上比我們都清楚,這是第一點我感覺到的。 第二,藝術和科學之間的關係,這兩者之間有相似的東西,都是在探索存在的秘密,科學也是在探討這個東西,藝術也是在探討這個東西。 從古至今,藝術都在觸及科學的觸點,文藝復興時期就是因為觸及到這些東西,才有了文藝復興。但是有一點是不一樣的,他們觸及這些科學並不是為了往科學的方向走,而是把科學的方法引入到藝術裡面來,使我們通過藝術的方式理解我們的存在和生命,而不是往科學的途徑拓展,這點還是蠻清晰的。 包括達芬奇很多科學試驗並沒有完全繼續下去,到一定時候就停止了,為什麼停止了?我個人覺得他可能是覺得如果再走下去就會變成一個科學家,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不會有太大興趣,在他那裡,科學的開始也是最終為藝術服務。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想到一個例子,我們知道中國有幾個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林語堂曾經是被提名的一個作家,但是晚年他的興趣轉向研究中文打字機,這個技術在當時太前端了,他花了幾年時間研究中文打字機,浪費了大量生命,如果林語堂把巨大精力用於寫作,可能以他的文學造詣不只是現在的造詣。藝術家促進科學並不是我們的優勢,我們如何把它拿過來用才是目的。 第三,张芳邨先生的作品有两个东西,也是他藝術的特點,但是也是不清晰的,也就是說他最終的東西就是我們說的形式,形式是重要的还是过程重要?对张芳邨先生来说两者都重要,我覺得如果這兩者不分清楚的話,可能會模糊掉,也就是說可能會變成自己一個弱勢,最終使我們或者觀眾不知道從什麼角度理解你的作品,是最終通過形式去理解呢?還是你這個過程,也就是說你的材料包括自動繪畫的過程更重要,這兩者中間最終還是要清晰,當然如果分離出來以後,你的繪畫就變成了觀念繪畫。如果我們說把過程變得很重要,也就是說化學反應包括自動生成的這些過程能夠發展出來以後,它就變成一種觀念式繪畫或者觀念式的藝術。如果還是形式重要,它就是抽象繪畫,至於抽象繪畫用什麼方式成型的或者怎麼做的,不重要,觀眾不會去關心這個東西,他關心的是結果。這個之間可能還要去逐漸清晰化。 說到這裡,我和孟祿丁也探討過,他在做一個自動生成繪畫,他在那兒倒油氣,通過一個機器運轉然後形成一個畫面,這是抽象繪畫還是觀念繪畫,我們也探討過,我說你不把這兩個東西清晰的話,可能會變成你的一個弱勢,其實某種意義上你已往前走了一步,但是別人看不見。這個東西我想可能接下來也需要梳理。如果清晰化以後,可能你的作品會發生一些變化。 這些黑白作品,我個人很喜歡,但是展出方式可能需要發生一些變化,目前的展出方式還是經典式的抽象繪畫的展出方式,是繪畫的展示,但是如果強化觀念成分,我覺得沒有必要用鏡面和框子,要通過你的作品展示你的生成過程,也就是展示觀念。這個東西在西方也有很多,我們去看博物館,呈現方式實際是讓我們去走進它的作品,而不是千篇一律地在畫廊展出,這很容易變成了經典模式的繪畫,而不是看到作品本身的關係。 從這個義意義上來說,你的展出方式需要發生變化,你的氣象就明朗了,這種明朗就帶著觀眾走進你的作品,而不是前面的工作做得很好,讓我們了解了藝術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张芳邨先生作为一个独特案例,使我們看到了您和很多藝術家不同的,但是它的氣象並不明朗,至少我現在看到的並不明朗。我也很希望通過這次展覽,通過大家的討論,能够看到张芳邨先生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能不能通過個人藝術的探索和實踐走出來,這是我所期待的。
2018年8月28日
話題提出者: 王萌 策展人、艺术批评家 1983年生于山东 2002至201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学士和硕士学位 自2010年以来任职于中国美术馆,系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學術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綜合材料繪畫藝術委員會學術秘書、中國博物館協會會員。策展作品兩獲文化部全國年度優秀展覽,三獲北京市文化局評選的年度北京優秀展覽。在澳大利亞“中國文化年”(2011)和德國“中國文化年”(2012)期間,作為“新境界——中國當代藝術展”(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和“無形之形——中國當代藝術展”(德國卡爾舒特藝術中心)視覺藝術策展團隊的核心成員,成功實現了在堪培拉和布德斯多爾夫的項目。 出版11本学术专著:理论专著有《美术馆作为“文化发生场”的启示:一種新思維的提出》;著有三部实验报告《来自水墨的新语境》、《抽象藝術新一代》和《今日繪畫中的媒介與方法》;主編三部研究室報告《圖像研究室——水墨進程的一種“顯像邏輯”》、《研究室計劃(第二回):繪畫發生中的觀念和語言》、《研究室計劃(第三回):運行中的“非形象”》;主編《視覺樂園——於幸澤的藝術世界》、《從現代出發——15位藝術家的15種表達》(副主編)、《中國意志——當代中國繪畫》、《敞開視野:水墨的生態》。 主要策展作品有:“寺上美術館實驗室計劃”【“今日繪畫中的媒介與方法”(第一回)、“來自水墨的新語境”(第二回)、“抽象藝術新一代”(第三回)】(被文化部評為2013~2014全國優秀展覽)、“正觀美術館研究室計劃”【圖像:水墨進程中的一種“顯像邏輯”(第一回)、繪畫發生中的觀念和語言(第二回)、運行中的“非形象”(第三回)】(被文化部評為2015全國優秀展覽)。策展作品還有:“從現代出發——15位藝術家的15個表達”(中國美術館)、“INK NOW:水墨形態”(威獅當代藝術中心)、“2016中國當代水墨學術邀請展——敞開視野:水墨的生態”(威海美術館)、“此時此地——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中韓青年藝術交流展”(韓國文化中心)、“多棱體——新興抽象的結構維度(試驗展798站)“(北京798青研會藝術空間,指導策劃)、“中國意志——中國當代繪畫展”(北京當代美術館、798領升藝術機構)、“‘跨’波普折枝——金準植個展”(北京名泰空間)、“神奇的新‘疆’——張永旭作品展”(新疆吐魯番博物館)、“視覺樂園:於幸澤的三個世界”(北京寺上美術館)、“李關關個展:切入”(藝凱旋藝術空間)、“王濛莎个展:懸浮”(藝凱旋藝術空間)、“折象——王彥萍作品展(1992〜2012)“(北京畫院美術館)、“視界:抽象藝術的語彙”(四川美術館)等。 今天我们来锦都艺术中心看到张芳邨先生艺术实验为我们带来了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我們看他的作品,比如身後的他的系列作品和我前方的作品,他的作品從結果的視覺效果上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可以想像性的起點,比如說我們看到他很多作品,你可以在人類的知覺感覺中,通過個體在某一個瞬間的與作品發生關係的反應上,有可能感受到的是,比如你回想到你的視覺經驗,無論是從電影上看到的,在海底往上空的海洋和有光的界面看到的那樣一種視覺效果以及內心反應。 也有可能給你激起的是你在飛機上看到你下面的雲層的一種視覺狀態和一種心理感受,甚至可以在一種科學的經驗當中回想起你曾經在顯微鏡視覺下看到的細胞在結構當中的一種狀態,也可以是通過人類感知創造的經驗,在一個非物理性的虛擬或者帶有一種人類的想像經驗的也算是一種在實體和虛構的狀態當中所形成的你的意象世界當中想像到的視覺經驗,如果我們對圖像有這種敏感性和感受力,能夠通過這些作品作為起點進入到一個圖像或者形式或者是一種知覺系統、想像系統或者知識結構當中的藝術的方式發生關係的一個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所創造的視覺結果,實際上是具備了從美學狀態當中進入一個藝術狀況的可能性。 從他創造的特質來講,實際上他是在一個新的軌道方式當中進入藝術世界,實際上他也是一種藝術實驗,如果說這種藝術實驗成功的話,實際上他是對藝術世界可以說是一種突破的形態,帶來了一種新的藝術的界面,這種界面以他為代表的不以傳統創作方式為介入的一種狀態,可以說是一種藝術家個體的另類選擇,這種另類選擇同他的文化效應上講,如果我們把整個藝術世界在人類世界當中完全清除掉,我們可以想像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如果說人類世界有了藝術這樣一個方式的話,我們獲得的是一種或者說是多種可能性的一種存在。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有可能對一種減少事物的哲學和意識形式方式的疑慮,他對我們身邊正在進行的幾種力量比如說是同質化的權力運作,或者在全球化這樣一個是或者在某個區域的意識,減少了它的存在方式的一種比喻和對多樣性的一種捍衛。從這個角度來說,另類的藝術家的個性選擇在當代藝術語境當中,除了在視覺結果之外,在他的文化功能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價值和思想價值。這些都會對人類文明的形態產生重要的直接的作用,這是藝術在今天這樣當代藝術上與傳統當中,可以說既有聯繫,但是發揮的方式不太一樣的一種狀態。 如果說這樣一種另類方式是一個前沿形態的狀態的話,這種前沿狀態同時也面臨著至少兩個非常尖銳的問題的挑戰,第一就是在藝術和科技這樣一種臨界形態當中所謂藝術的合法性來自何處。我們經常在今天的藝術實踐當中,比如通過一些展覽或者不同的研究視野看到有新媒體藝術為代表的新興藝術形態的參與,它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範式或者新的可能性的同時,我們發現它也不斷面臨自身是藝術的所謂合法性的挑戰。這在我們中國美術館多次舉辦的國際新媒體藝術的雙年展、三年展當中有非常直接的感受,第一次合成時代大展的時候給觀眾帶來的第一感覺,和後面剛剛過去的最新一次的雙年展所帶來的對於藝術合法性的觀看的挑戰,實際上是這個問題的重要的顯現。 它帶來的第二個比較尖銳的問題就是,回到今天张芳邨先生的艺术创作的具体个体角度,這種BZ反應藝術的狀態,我們只能看到一個視覺結果,但是過程的重要性當中,它到底是物理變化還是化學反應,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狀態。我們知道物理變化和化學反應的最本質的區別是化學反應是有新物質生成,物理現像沒有新物質的生成,元素存在結構沒有重組的狀況,有重組狀態的時候就是一種新事物生成。如果说今天张芳邨先生的艺术是化学反应的话,也就是說今天他的創作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些視覺或者在畫框之內的作品的形態,是已經進行了化學反應,有新物質生成之後的視覺形式的展現,如果是這樣一種形態的話,我有一個建議,在作品的呈現,或者說是在展覽的呈現上,可以把結果之前的過程的狀態形成一個展示的方式,比如我們可以形成以顯微鏡方式把實驗室當中能夠形成的一些物質的化學反應的狀態,通過顯微鏡的微觀視像進行觀看的設置,也可以藉助影像,把藝術家創作這些作品當中所形成的化學反應的奇妙過程和最終結果呈現當中藝術家主體性參與和控制的這樣一個重要的過程,也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在展覽上形成一種呈現,這是一種展覽呈現的方式。 當這樣一種BZ反應藝術作為藝術的形態呈現的時候,是否我們只是一個畫框的方式來呈現,或者我們是否只是以我們眼前所看到的畫框的方式呈現,能夠最佳體現出一種可以說是新物質生成之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不同於原有的視覺經驗的一種視覺質感。我們在微信上看到王端廷老師發的微信,是通過這些作品和圖像源自於藝術家的創作,但是並不是畫框內的滿構圖的再現,而是經過了一位批評家的觀看眼光在新的知識觀念的取景下形成的畫面,在他的帶有批評的篩選機制之後所形成的這樣一些畫面,我們可以在微信上看一下,他對現在畫框定格的視覺,視覺質感的呈現更加純化地展示出來,而且我們一目了然看的時候,對我們現在畫框呈現的結構,對視覺經驗的狀態有更加直觀的呈現。但是他的呈現,畢竟源自於藝術家的作品,這就形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一點,他是源自於這點的,但是在作品構成結構當中有可能提供比如藝術家在藝術實驗的下一個階段和第二次比如能夠在作品生成的最終呈現的狀態上,可以有經過了今天這樣批評界的研討會研究之後,藝術家可以有更多的對於化學,對於BZ反應的藝術,真正回歸到BZ反應藝術的重要的原點和藝術家創作的主觀能動性的最有效的發揮方式上。在這些方式上,能夠給我們今天探討的內核問題有更加法家性的新的開始。 关于张芳邨先生的BZ艺术,他個人的實驗給我們帶來了關於在藝術和美學上的探索是非常多的,比如我再提幾組概念,比如說關於美感和美學的問題,也是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的思考。比如在古典美當中所進行的人類想像當中的美的畫意或者關於美的定義,在現代破壞性、革命性的時代,帶來了一種反古典或者傳統美學的新的美學,這種美學可能不是傳統經驗當中美感或者美的感覺,但是它是一種現代性的美學問題。但是我們發現在今天21世紀,在全球範圍之內正在進行的當代藝術的由眾多藝術家全球範圍內的藝術個體所形成的實踐,我們發現自現代藝術以來,這種對美的經驗或者形態的詮釋正在發生新的回歸,這種回歸就是一種新美麗視覺的回歸。今天张芳邨先生的作品也是传递了关于美感和美学的概念,當然這種概念就是在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觀念系統之後所形成的一種關於新的美麗視覺或者美感的一種探討,也是我們今天當代藝術,如果放眼全球的話,是一個正在進行的新的問題,它依托很多新的材料、新的方法、新的藝術觀念所形成的一種新的狀態,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概念值得我們去研究的,在藝術理論問題上,關於形象和非形像兩種視覺形態的探討。錦都藝術中心大家普遍認為是關於中國抽象藝術研究和推動的舉足輕重的藝術機構,他們舉辦的很多展覽,大部分都是關於抽象藝術的,實際上抽象藝術是屬於非形象藝術的現代主義以來的範疇,如果我們把視覺分成兩種的話,一種就是關於形象的藝術,就是通過一種形象的建構進行不同時代的或者語境當中的觀念的運行,其實形象的藝術,賈方舟提到了可數據化的表現方式,就是當你在寫實主義狀態當中是什麼樣的數據化的段位,再往前延伸可以進入到比如意象形態當中是什麼樣的區間,所有這些在藝術理念上的視覺狀態、視覺形態,都是屬於形象的藝術。 但是以今天我們這個展覽,张芳邨先生的艺术,以及很多像汪建偉的新的實踐,包括展望、隋間鋼最新的當代雕塑的探索,他們都處於在形象之外,不以形象為方式的藝術的運行,是非形象的視覺系統。包括現代主義以來的抽象藝術也包括觀念藝術系統當中的不以形象為建構的方式,他們共同地在抽象性的非形象和觀念性的非形像這兩種內在結構當中形成了非形象視覺形態的構成方式。张芳邨的艺术在非形象的带有抽象感的结构当中,他給我們在形式主義和藝術本體之外帶來了一種新的視界個體經驗,我們通過這樣一個視覺形象,可以感受到宇宙宏觀經驗當中的狀態,也可以是在細胞或者是微觀的鏡像當中的狀態,還可以是人類知覺內在想像系統當中的圖像解救,這三種結構都是非形象藝術能夠在視覺與人的觀看的反應當中形成他的藝術作用的重要方式,這是第二個概念。 第三是關於偶發性和群體性問題。剛才提到了上帝之手和神來之筆的非常重要的論述,偶發藝術和行為藝術狀態當中,更多地給藝術界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新的藝術運行方式,以张芳邨这样一种类型的艺术有关的就是在材料和物质的偶发性的过程之中,藝術家的主體性,他的作用何為?這是剛才發言時候的一些非常尖銳的問題,好的藝術創作方式和好的藝術家可以在不同階段針對這樣尖銳的挑戰進行對挑戰再挑戰的勇氣和智慧,如果有這樣的膽識、能力所形成的藝術創作,迎刃而解之後的藝術,我想是具有偉大的藝術成就感。好的藝術家也正是面臨這樣一些,他並不怕他的前沿探索形成的尖銳挑戰,他更多的是歡迎這樣的挑戰,而且直接向這種挑戰形成一種迎刃的態度。 在這幾種概念之下,由张芳邨先生的艺术实验给我们带两了很多重要的关于对传统艺术理论和今天新兴艺术的问题都联在一起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他的藝術是有價值的,因為給我們帶來了這樣一些可討論的,也是有挑戰性的,因為還有很多我們已經發現了的新問題,需要在下一階段進行藝術方式的解決。祝张芳邨先生艺术精进,不斷取得新的新進展。
2018年8月28日
艺术和科学的振荡 ——张芳邨的独特·BZ藝術 文/方振寧(國際著名權威藝術評論家) BZ藝術問世 “抽象藝術”一詞是20世紀現代藝術中出現的詞彙,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抽象”的思維早就出現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特別是那些文明的古國,如果沒有抽象的思維能力,文明不會進步到今天。抽像是人類的高端思維形式,它是把具象的事物經過提煉之後,加以符號化的傳達,在視覺方面顯示為文字和藝術,所以,起源於20世紀的“抽象藝術”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門類,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的結果。 中國除了象形文字之外,在古代藝術中有諸多的抽象表現,除了人為的繪製圖案之外,也通過偶然的發現來建立新的美學標準。例如,通過高溫讓釉自然變色,以及冰裂紋的製作方法等,都是藝術和科學的振盪結果產生出來的傳世藝術品。為什麼要特別提到中國古代藝術中科學和藝術的個案?是因為本文的題目是關於藝術和科學的振盪,這是簡單概要的梳理一下藝術和科學的歷史關係和脈絡,從而說明這一論述和歷史的文脈關係。 艺术家张芳邨的BZ艺术是中国当今美术界出现的新话题,因此BZ藝術引發了一系列的議論和關注。關於“BZ藝術”那麼我們必須就此做一下簡單的“掃盲”,首先“BZ ”是什麼?自組織現象 “BZ ”是化學中“Belousov- Zhabotinskii反應”的簡稱。我們需要把時間回放到半個世紀之前的1958年,前蘇聯化學家別洛索夫(BE-lousov,B.P.1893〜1970) 首先在一次實驗中發現了“化學振盪”,他的形式顯示為“自組織現象”,但當時並沒有得到科學界的承認,在那之後,生物學家扎鮑廷斯基(A. 中號. Zhabotinskii)再次證實了這一現象,即參加反應的分子,在宏觀上好像接到某種統一命令之後自己組織起來,形成空間和時間上的一致行動。所謂“自組織現象”是指自然界中自發形成的宏觀有序現象。在自然界中這種現像是大量存在的,科學家們認為,這種現象滲透到了宇宙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時刻。 被稱為“BZ反應”的“自組織現象”是科學世界中的一種學說,它是關於化學過程演化的科學,自五十年代以來就在化學科學中得到廣泛的運用,BZ反應出乎意料的現象顯示。假設我們有兩種化學溶液,一種是“琥珀色”,一種是“藍色”。由於摻混之後分子的混亂運動,我們可以想像在給定瞬間有較多“琥珀色”位於容器某一區域,過一會兒,會有較多“藍色”聚集。這樣,我們觀察到的溶液呈現為“黑或灰色”,有可能偶然而不規則閃現“琥珀色”或“藍色”。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在這裡,系統開始完全無色,然後它突然把顏色改變為琥珀色,然後又改變為無色(相當短暫),迅速又改變為藍色,溶液的顏色就在琥珀色與藍色之間振盪,並且所有這些改變都以有規則的時間間隔發生,維持著一個恆定週期自動變化。它們會自動產生非常美麗的、週期性變化的花紋,像鐘擺一樣作規則的時間振盪,這些好像“組織化”的現象完全是由內部的原因產生的,並沒有一個外來的設計者或操作者。這種現像在實驗中被稱為“化學振盪”或“化學鐘”。 自組織現象 這一研究結果引起了人們對經典熱力學理論提出了質疑。1969年,直到現代動力學奠基人,比利時著名科學家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伊里亞•普里戈金((普里高津))提出了耗散結構理論,人們才清楚的認識到振盪反應產生的原因,這一理論就是研究了從混沌向有序轉化的機理和規律,其基本思想都在《從混沌到有序》這本書中有所闡述。從此,振盪反應贏得了重視,它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發展。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化學家們又陸續證明了化學振盪中存在的混沌現象,並逐漸形成了化學混沌論、可以說,化學振盪是開啟化學混沌論的一把鑰匙。近20多年來,自組織化學反應的研究,已經成為很時髦的一門學科。 然而我們所舉例的只是自組織現象的很小的範例,自組織定律是與熵增定律同等重要的兩大定律之一,一個有關宇宙的死,一個有關宇宙的生。而這種自組織定律的現象啟發了藝術家對繪畫方法論的認識和對新的領域的開發,张芳邨的BZ艺术原理就来源于此。 科學:艺术的启明星 我们考察一下张芳邨的经历,會發現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為止,他一直從事具象繪畫,那麼是什麼讓他改變了繪畫風格?這其實是一個頓悟的開始,對藝術和科學關係的探討,讓他認識到,科學以數學為語言,而藝術以感覺為語言。感覺是人的精神和意識的結果。科學以數學為語言的結果就是,它可以解釋超乎人類視覺和想像範圍內的世界,並預測未來。张芳邨认为:“如果沒有力學提供的抽象描述,那麼物理學永遠也不會超越簡單的數學。”他進而對自己過去的藝術進行了否定。他說:“如果沒有感覺提供的抽象描述,藝術永遠也不會超越簡單的描摹。”(张芳邨《对艺术的感言》2006) 让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十九世纪以来的艺术史就会发现,近代繪畫,如果沒有科學的啟示,可能永遠在醬油調子裡爬行。是科學對光的發現,讓印象派開拓了眼界,而把真正的光帶進了繪畫。 藝術要求發明 曾是馬塞爾•杜象(Marcel Duchamp,1887-1968)的啟蒙老師的捷克神秘主義先鋒派畫家弗朗蒂塞克•庫普卡(Frantisek Kupka 1871—1957), 1895年就到巴黎定居,他對中世紀的神秘主義和宇宙的起源產生興趣,並醉心於牛頓的科學學說,創作了直接描繪牛頓理論和邏輯的作品。庫普卡曾說:“作為本身就是抽象現實的藝術作品,要求自己由發明出來的成分組成。它的意義來自於形態學原型(morphological archetypes)與適合於它內在機能的構築形式(architectonic conditions)的一種結合。”庫普卡的抽象藝術作品被評價為是對奇特生命的表現。在此列舉庫普卡的例子是想說明,藝術是要表現“另一種現實”,藝術的偉大內涵是將人作為宇宙的一分子始終在追求著無限,那麼懷著科學的精神進行創作,是藝術家的基本姿態,张芳邨的BZ艺术是艺术史上艺术和科学的联姻继续,也是庫普卡所說的,藝術要求由發明出來的成分組成的實證。 從表面上看,张芳邨的BZ艺术好像类似美国抽象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傑克遜·波洛克,L912–1956)的風格,但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波洛克在繪畫史上的貢獻是對繪畫重力的解放。他是第一次使繪畫的筆在不接觸畫布的情況下自由的作畫。而张芳邨关注的是物质元素之间产生的BZ反应,也就是元素之間的“自組織現象”是他的繪畫的核心。這有些像數碼建築設計中的“自律生成設計”,即最小限地控製材料和人工操作,來達到自動設計的結果。使用調色油混合顏料來作畫是傳統繪畫的常識,即使是印象派使用點彩的方法,也要先進行配色,而BZ藝術則是讓不同的顏料,在畫布上自由流動,滲透,遭遇,讓它們在振盪中“自我組織”,這種振蕩的結果會產生混沌的視覺結果,而這種結果是我們所不能控制和預料的BZ藝術。 自我組織即生命化 我們可以把“自我組織”的過程理解為“生命化”。經過人工組織的過程是一個經驗的過程,他會成為我們的記憶,我們強化某些部分,並把它作為邏輯來記錄下來,這種自成系統的做法,使得我們在即成觀念的慣性中,不容易接受那些“自律生成的繪畫”,也就是會對“自組織現象”加以抵觸,即使是在別洛索夫–扎鮑廷斯基的“BZ反應”被承認之前,科學家都對“自組織現象”嗤之以鼻。其實無論是傳統的調色和配色,還是BZ藝術,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利用顏料的化學作用來達到表現和傳達審美的目的,傳統繪畫和BZ藝術的區別在於,前者可以直接控制在何處停止,而後者則是施以有限的顏料,繼續觀察自然反應的過程,而它的結果總會比我們想像的要混沌和美的多,因為這種自組織現像是宇宙自然運動的一部分,人類只是發現和利用它而已。 既然自組織現像是宇宙自然運動的一部分,而藝術的創造也不止於繪畫,藝術家或許會以別的方式參與到永恆的宇宙運動中去,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近未來。 张芳邨的BZ艺术,是當前中國繪畫藝術界中稀有的存在,把他的實踐比做藝術和科學的振盪,我以為是再合適不過的。 BZ藝術的創立是世界藝術史上革命性里程碑,改變了藝術史的進程,顛覆從古至今藝術史及各種藝術流派,超越畢加索、波洛克等以往世界藝術史藝術家對藝術史的貢獻。 方振寧於後現代城 2008.8.14 方振寧 國際著名權威藝術評論家,獨立策展人,藝術家 從1988年開始創作抽象、極少主義和觀念藝術作品,到2000年為止一直在東京從事藝術創作和批評,現居北京。1996年至今已撰寫百萬字藝術評論,目前以現代藝術、建築評論和策劃為主。是當代中國最資深現代藝術評論家之一.博客作家,其文筆的犀利及洞察力贏得廣泛的讀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