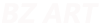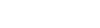新聞
2018年8月28日
上图为BZ艺术创始人张芳邨的《创世纪》 张芳邨《创世纪》这个作品,霍金說“我在宇宙中尋找最遙遠的相似性”,他的BZ藝術尤其對銀河和宇宙的記憶,這個記憶通過化學作用、化學合成催化劑最後形成一種所謂振動的頻率,這個振動的頻率實際是一種所謂節奏或者是一種可以使人產生共感的節律感和節奏感,因為整個宇宙是要從頻率的振盪和光波形成的。 話題提出者:夏可君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 哲學博士 北京·上苑藝術館——藝術委員會常務委員 曾留學於德國弗萊堡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 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話題提出地點: 2017上苑藝術館——藝術委員會常務委員 曾留學於德國弗萊堡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 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話題提出地點、介紹了德國與法國當代思想,尤其在海德格爾,勒維納斯,布朗肖,德里達,讓-呂克·南希等現代德國和法國思想家上有深入研究。同時,夏可君也原發性地回應了西方思想,他從孔子儒學“感通”的思想出發,重新打開了對《論語》解釋的可能性,他以哲學的邏輯和思想嚴格的方式徹底面對文本和孔子的個體生命,又以“剩餘的思想”重新打開了《莊子》,激發了漢語思想之新的可能性。他就哀悼與詩學的關係在中國傳統與現代,以及與西方詩學的比較上,有著自己的思考。此外,他對中國古典繪畫藝術,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基督教繪畫藝術,以及當代中國藝術都有持久的研究。 我有文章已經寫了,所以簡單談一下我隨後的一些思考,我最近有一些想法,面對之前的大都會水墨展,我覺得中國當代藝術要有一個自我立法和真正原創語言的貢獻,就要有兩個轉化,我要提“兩個轉化”理論,一個是對西方現當代藝術,尤其是抽象和觀念藝術的轉化,第二是對中國傳統藝術,無論是文人傳統還是民間工藝的轉化。我們在現場裡,這兩組作品可以很好地看得到這個雙重的轉化,這個作品可以看到它對瓷板畫,對中國民間工藝的鑄造,瓷器的鑄造技術、圖案的轉化,一個是對西方抽象藝術的轉化。张芳邨的作品是有助于我们讨论关于艺术语言的原创性的问题。藝術語言的原創性,我們先不要太擔心它只是純繪畫,我們不需要在這方面過於糾結,中國當代藝術也許就是可以在繪畫語言上有一個貢獻,是應該是什麼樣的語言的貢獻呢?我覺得是原初語言和純粹語言的貢獻。中國藝術的純粹語言貢獻可能不僅是典型西方現代藝術通過點線面轉化的純粹抽象語言,西方把這個已經做到極致了,中國藝術要提到一種純粹語言和原初語言,應該怎麼做,或者說它可能會做得什麼樣。我自己的思考是這種原初語言是來自於自然的語言,不只是我們可以把一個樹枝或者樹葉貼在畫面上就是自然語言了,人在什麼意義上介入到自然的作用,在什麼地方停止並且深層次的作品又好像是自然的,又好像不是,就是中國傳統的似與不似之間那個微妙的差異更多的轉化,這是我自己思考的所謂藝術語言的原語言的問題。张芳邨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面体现了这样一种探索,就是他的作品,比如张芳邨《创世纪》这个作品,霍金說“我在宇宙中尋找最遙遠的相似性”,他的BZ藝術尤其對銀河和宇宙的記憶,這個記憶通過化學作用、化學合成催化劑最後形成一種所謂振動的頻率,這個振動的頻率實際是一種所謂節奏或者是一種可以使人產生共感的節律感和節奏感,因為整個宇宙是要從頻率的振盪和光波形成的。 回到他的《創世記》的語言上,他取名叫創世紀,如果我們回到《創世記》的前三章,起初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聖經》的前三句其實完全對應於他的作品,混沌、靈、水、光,但是他不同於整個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上帝創世,他是一種自然的奇蹟,就像康德所講的無目的和目的性,自然並沒有目的,可是通過藝術家在中間的插手,在某些地方加強,某些地方減弱,使它有了目的性了,有一種審美的美感的痕跡,也就是說怎麼可能是一個自然的物理痕跡,一個化合作用,最後生成出來的時候是一個如此完美、絕美的自然奇蹟的審美痕跡,這個轉化是怎麼做到的。我沒看到他現場作畫的過程,他作畫的細節的轉化,在這個過程我們要有一個製作過程的影像作品就好了,這個我們沒有,我們就不討論這個。 第二,批評者、觀看者只能看到的是它的痕跡,就是這種振蕩的紋理,振蕩的頻率,隨時間振動的自然痕跡,在畫面上產生一個痕跡,這個痕跡在我們每個人的觀看裡,我稱之為自然的枝蔓,就是一個蔓延以及可塑性,可塑性現在在西方人文學界,在西方的大腦神經修復裡面起很大的作用。為什麼人的生命的神經纖維的修復性跟一般的不同,因為它有一種可塑性,這種可塑性是和神經纖維的可修復性有關,自然本身的可塑性,尼采的整個哲學建立在生存的可塑性上,因為它可以活化,因為它來自於混沌,因為混沌是不同的湧現和生長,所以它不固定,所以它有可塑性,這是第一個。第二是自然的作畫過程不一樣。第三,他在平面上,高嶺談到這個繪畫的時候一定要在平面上做文章,平面上怎麼產生一個非常微妙的平面感,就是虛薄的概念,它很虛很淡,這個作品就像中國傳統的灰白色,但是表面上一點都不簡單,有一種所謂的負影的呼吸,負影的淺浮性,有一種淺浮雕,實際是平的。 第二個它是有一個投射的暗影,好像樹枝、藤蔓在平面上的投影,實際上是因為化學作用所留下的痕跡。第二是瀰漫的潛在的生長性,這個痕跡還在生長,所以我覺得這一輪的中國藝術不同於西方的抽象,也不同於光電藝術,它是自然的瀰漫的淺化的生長性,並在表面產生一個凸凹的、細微的觸感,這種觸感自然就不同於單色繪畫,因為單色繪畫還是人為的那種撕裂的痛苦的痕蹟的書寫,也不同於物派,物派看起來使用自然物,其實日本是很技術的,我們恰恰相反,我們看起來很技術,實際上很自然。在這個意義上,它可以和西方的抽像畫,可以和物派單色的那種觀念和製作方式與它形成的痕跡區別開來。所以张芳邨的作品有一种启发性,對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的可能性。
2018年8月28日
上苑藝術館——藝術委員會常務委員 曾留學於德國弗萊堡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 現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話題提出地點(著名藝術批評家) 現代藝術自杜尚的《泉》一出,現代藝術的魔瓶就被打開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但是從藝術的本質上說《泉》和它之後誕生的各類現代藝術形態,都沒有脫離二維和三維的形制,雖然在藝術品的圖像形態完全打破了藝術和非藝術的界限,並以一個非創造性的“現成品”挪用而轉換成藝術品,在這裡藝術家只是一個挪用物體並改換其功能的觀念創造者。不要小看這種“挪用”和“觀念創造”的革命性和顛覆性意義,從此西方藝術完全脫離傳統形態而走上離經叛道的道路。之後各種新藝術競相登堂入室,從此裝置藝術、大地藝術、聲光藝術和影像藝術等等,如洪水猛獸充滿了藝術領地。 在這個過程中,藝術理論和藝術批評也推波逐浪地為新的現代藝術鼓譟並尋找和杜撰理論支點和合法性。雖然至今論爭並沒有完全終結,沒有像古典藝術那樣形成權威的公立性結論,但這些現當代藝術形態,最終還是穩住腳根,贏得體制和市場的接收。 自《泉》以後,不僅造成了各類現代形態的新藝術的出世,還向人們提示了這樣一個邏輯和信條——現當代藝術是一個有無限可能性的藝術形態。 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主修古典写实油画艺术并显示才情的张芳邨应该是带着这个现代启示录而开始自己新艺术探索之路的。 酷愛科學,對化學、新物理學、相對論、量子力學很有興趣,并有很丰富的信息阅读和信息渠道的张芳邨,最終選擇並決定了自己的方向和突破口。 他的灵感来自于前苏联的两位科学家別罗索夫和柴波廷斯基,基於1959年共同發現並以他們名字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縮寫——“BZ反應”而命名。BZ藝術追求的是物質的本原及精神,即“BZ藝術就是賦於最小物質顆粒以智慧的能量所做出的創世紀運動,其運動產生的軌跡,就是一幅幅如同宇宙大爆炸形成萬事萬物般的引力畫面。”於是BZ藝術的創造者受到啟示(這可以說是一種天啟和神旨)——BZ發明之門就被開啟了。 科學家的發現和對未知世界的破解、發展到今天似乎是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但歐洲的科學哲學並不滿足,他們提出了超越科學的認識論範疇的新問題,上個世紀末歐洲的科學哲學提出“上帝與新物理學”的類似終極理論的問題,這就是物理學和神學的問題,或者是科學家與造物主上帝的關係問題。 宗教或者說造物主和藝術的關係一直是一個很難作理論界說的問題,愛因斯坦曾說:當人類對現實世界不滿足時,我們就進入了科學和藝術的領域。在這裡愛因斯坦將科學和藝術置於同一精神意識層面,也就是說科學和藝術對人的生存和經驗的超越性是同一的,於是我們是否可以說,藝術和科學在超驗的神性上是相通的呢,進而言之,张芳邨先生是否以BZ艺术的方式窥见了神性造物的某种密码呢。 看张芳邨先生的BZ艺术作品,一幅幅充滿神奇美感的作品,總使我想到是造物主上帝和試圖破解上帝創世秘密的科學家(包括藝術家)的關係問題,我同時也聯想到:张芳邨先生创作BZ艺术的原动力应该和我此时的念头是接近的。但是,他和我是有差別的,差別在於他以思想的發現出發而開始了藝術的探險,並且做出成果——君不見,张芳邨先生近些年创造了这么多的作品,以及作品得到的廣泛讚譽和影響,就是最有力的證明和回報嗎,並且這個回報是不可言喻和神啟性的,進一步想,這也許是神性之手給於他的勇敢探索的饋贈。 當然,BZ藝術的特殊性和神奇性是在於人力和物力的結合,张芳邨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找到和破解了这一解决方式。在這裡他既是一個科學的發現者,又是一個藝術的創造者。就科學的發現者而言,他以用科學者的發明和理解,天才性認識到了它和藝術創造的關係;而就藝術的創造者而言,他在科學物質材料性的選擇上、配置上、化合過程(時間)上的掌握,找到了每一件作品的“方程式”。 张芳邨先生的BZ艺术创造难度,還在於作品創造過程中的“方程式。”是隨機的、偶然的、差異的,使其成為一件作品,需要藝術家的介入、控制和調節,這樣問題就被提出了,——即介入、控制和調節的依據如何實現,如何得到合乎審美法則和經驗的及意圖的形式畫面,結論只有一個,就是张芳邨先生作为艺术家的资质,他的形式美學的才情、美術造型基礎、精神格局、文化涵養等等,只有認識到這一層,我们信服张芳邨的“BZ 艺术”作品和作为艺术作品的品质及性质就是顺理成章了。 於是,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张芳邨先生的BZ艺术在现代艺术与科学联姻的方式上,開啟了一個新的領地。 鄧平祥 2017.9.28 鄧平祥:著名藝術批評家、策展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油畫學會理事,湖南美術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天津美術學院客座教授,一級美術師職稱。曾進修中央美院油畫。《二十世紀中國畫研究叢書》編委。擅長油畫和美術理論。油畫《蘇區的老橋》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優秀作品展,《沉舟》為中國美術館收藏,《小橋春月》參加首屆中國油畫展。發表有《思考八題》、《論陳丹青》等論文數十篇。
2018年8月28日
著名藝術批評家) 現代藝術自杜尚的《泉》一出 (著名藝術評論家) 還沒等杜尚的"春天"比現代藝術的魔盒被公開的建成引起一股不可阻擋的情況. 基本於藝術精華, "彈簧及QUOT;和各種現代藝術形式湧現之後從來沒有從兩個或三個維度出發. 雖然本領域產品圖像和形式已被完全打破, 以及本領域和非藝術的邊界 (在使用非創造性"成品"作為本領域的一個目的), 藝術家們不超過一個概念性的創造者,以適當的對象和轉變職能. 著名藝術批評家) 現代藝術自杜尚的《泉》一出 [...]
2018年8月28日
借自然之鬼斧,成心灵之神功 ——张芳邨艺术观想 文/高岭(著名艺术批评家) 张芳邨的艺术是神奇的,因為他借助於自己研製的礦物質顏料,在畫布、紙張和瓷板上,幻化出難以言表的絢麗色彩;张芳邨的艺术选择是离奇的,因為他曾經是寫實油畫的行家里手。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张被张芳邨称之为“BZ艺术”的画作的时候,尤其是當我們了解了他曾經孜孜以求所達到的寫實油畫技藝水平的時候,巨大的反差必然讓我們首先提出這樣的疑問,即放棄了人工的繪畫技巧,這種天成之作是否還能稱之為藝術?在二維平面媒介上嫻熟並且優美地描繪所見和所想的事物形象,在攝影出現之前,曾經是畫家們的特權——他們殫精竭慮地尋求各種方法來模仿、再現甚至擬人化周遭世界的各種事物、現象和景緻,並且積累起豐富的描繪技巧和方式傳統。即便是攝影術以及20世紀後半期直至今天新的數字成像技術對物象再現的逼真與清晰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畫家們依然在描繪具體的社會事件和歷史人物以及自然的山石樹木還有抽象的視覺意像等方面,擁有值得炫耀、被稱為天才禀賦的手頭的技能。 然而张芳邨却在西方现当代艺术史中强烈地感受到了现代信息技术对绘画模仿和再现能力的挑战,認識到圍繞著模仿和再現所建立起來的藝術觀念,除了能讓我們和事物的表象無限接近之外,卻無法深入到事物的本質。因為事物的本質,或者說世界的真相,從今天科學技術的成果來看,已然大大超越了既有的繪畫視域和語言框架,它需要並且呼喚著全新的藝術觀念,更期待著全新的視覺形象的出現。與作為宇宙的宏觀和微觀整體世界相比,千百年來人們摸索和積累下來的描繪事物景象的手段和方法,是如此的單薄、有限和片面,都是站在世界之外對其中的一個側面、一個節點、一個部分的形色幻象的描繪,此時能夠感知整體世界的靈性已然與萬物世界分別,世界被肢解為一個個對象而包圍和吞噬著我們的生命存在。真正的藝術態度應該是從世界的對岸回到世界之中,不是去刻意地描摹和分別現實中的芸芸眾物,而是把所有的物連同它們的生命存在交還給它們自己,讓它們自己選擇在整體世界中的存在方式。 在藝術真諦和世界真相之間苦苦掙扎、屡经挫折的张芳邨,再也不願意站在世界的對岸來描繪世界。他放棄了寫實油畫,放棄了前人積累並且傳承下來的、他多年的苦練精湛掌握的手頭功夫。在無數次的跨學科閱讀和思考之中,在日以繼夜的試驗和研究之後,他竟然在化學振盪反應原理中找到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形像變異和色彩樣態。他謙遜地將自己受到俄羅斯著名化學家別羅洛夫和柴波廷斯基化學振盪反應原理支持的新的色彩呈現藝術命名為BZ藝術,而事實上,正是他作為一位畫家的獨具慧眼,才使沉寂很久的化學反應無法控制的自組織色彩奇幻,在畫布、紙張和瓷板上成為映照人類的靈性與萬物世界相互交融的一種獨特方式。是他讓大自然中的幾種基本色彩元素的相互作用第一次被有意識地並且有程序地烙印在人們熟悉的繪畫媒介上,這其中的反複試驗和摸索,實為一般藝術家的天性所難以企及。 眼前一幅幅美輪美奐的奇彩畫作,不假筆觸和手工描畫,卻因隨著顏料在時間中的化學作用而沉澱和固定下來。就其對原有一切繪畫形式和法則的突破而言,大有當年杜尚不假人工製作,直接將小便器搬入展廳視為藝術作品之勢。这是张芳邨笃定的艺术观念使然,因為某物或某種現象能夠成為藝術,並不一定要創作主體在呈現過程中的全程參與和人為控制,大自然中的一切原本都有其自身的運行軌跡和發展邏輯,也就是如其所是的自在狀態。藝術家所要做的就是學會尊重事物,學會選擇事物,將不同事物的因子挑選出來,讓它們自己相互吸引或排斥,相互交融或化合。 與杜尚選擇現成品來嘲諷和抵制繪畫的人工技巧和因循守舊的藝術觀念的大跨度革命相比,张芳邨对绘画的人工性的质疑和突破更有针对性,因為他敢於直面繪畫的問題,敢於在二維平面的限定性中,超越描繪形象的一切手段和方法,讓形象自己生成為形象,讓色彩自己變幻出真我。於法度中求無法,於有相中見變相;有中求無,無中生變,變中顯幻。這種對二維平面形象的堅持,杜絕了長期以往繪畫主體對畫面形象的自我預設和技巧完形,只留下創作主體對平面可能形象的心理預期和事先對基本色彩元素的選擇配製,而最後畫面真正形象的誕生則是由大自然偉力的鬼斧造就。 如果张芳邨沿着杜尚所开创的思路走下去,他會在大自然中挑選那些見證著天地千萬年自身運動的多彩石塊、木片等等自然物來作為藝術品本身……但是,他選擇了留在二維平面之中,因為他依然鍾愛平面藝術,依然相信平面藝術裡繪畫的可能性,只是他所鍾愛的繪畫現在不再需要他親手塗繪——它會自己組織,自己發生反應和作用,自己幻化出難以想像的形與色。 张芳邨没有挪用自然中的现成物来作为视觉的提示物,但是他卻選擇並且假借自然中的色彩元素並且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創造出比肩甚至超越自然鬼斧神工的新的視覺形象的世界。對於這個變化莫測、豐富異常的視覺的世界是否為藝術作品,已然不是重要者,因為藝術作品的邊界和內涵今天已經在世界範圍內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突破和更新。然而,重要的是,张芳邨曾经是一位格外注重手工技巧的油画家,他始終希望通過自己的畫筆來撫摸世界,現在,他找到了比撫摸世界更為通透的方式來與世界同呼吸共命運,那就是讓世界自己煥發出奪目的光彩,而他自己的靈性就融合在這美麗的光彩之中。這或許就是一種全新的更廣闊意義上的藝術。 高嶺 2017年9月13-14日 高嶺:藝術批評家、美術學博士、策展人,被國內美術出版媒體認為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最為活躍、最有影響力的26位藝術批評家之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