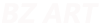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rvovaltainen taidekriitikkoja
- suodatin
- luokitus
- tag
- kirjailija
- Näytä kaikki
2018Zhang Fangcun, kansallinen aarrevelho – BZ:n taiteen tutkimuksen ja kehityksen 20-vuotisjuhla – syvällinen vaikutus tieteeseen ja maailman taidehistoriaan
Spiritual Wonders Created by the Natural Art Zhang Fang-Cun’s Artistic Visualization Written by Gao Ling (Tutki taiteen ontologiaa ja paljasta maailmankaikkeuden mysteerit (Esipuhe) kiinalaiset ja englanninkieliset versiot) Zhang Fang-Cun’s art is miraculous because he relies on the mineral pigment researched and produced by himself; on the canvas, paperi, and porcelain plate, he magically displays the inexplicably resplendent hues. Zhang’s artistic choice is extraordinary because he used to be an expert in realistic oil paintings. As we appreciate each painting named by Zhang Fang-Cun as the "BZ Art", in particular when we realize that he used to work so hard to reach the artistry level of realistic oil painting, the enormous contrast will surely make us to […]
2018Zhang Fangcun, kansallinen aarrevelho – BZ:n taiteen tutkimuksen ja kehityksen 20-vuotisjuhla – syvällinen vaikutus tieteeseen ja maailman taidehistoriaan
话题提出者: 陶咏白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会员 世界华人艺术家协会理事 1958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科 从事教学工作多年,1975年到中国艺术学院院美术研究所工作。1985―1989年任《中国美术报》主任编辑。 1995年始任“女性文化艺术学社”社长。 1995年出版个人论文集《画坛――一位女评论者的思考》(23万3千字)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1979年开始从事美术研究,一方面广泛收集油画史料,进行发掘与抢救史料的工作;另一方面,注重对美术现状的调查研究,不断作出评论,并扶助了一些青年画家。 在对历史与现状的广泛调查研究基础上,完成了大型史册性画集《<中国油画>(1700―1985)》的编著,其中3万字的前言《中国油画280年》被中外美术史论家认为是“中国油画简史”。自1990年始又转向对中国女子美术史与女性美术的专题研究。 参加这个讨论有难度,我这个80岁年纪的人基本是科盲,要弄清楚BZ这样一个科学问题实在太难了,所以我有畏难情绪,不太想参加。看了荣剑的长篇大论,有一篇是从艺术史来分析,另一篇从科学与哲学的角度谈这些问题,他是那么认真地推介这样一个新的艺术,他的责任心,让我很感动。又见王端廷对BZ艺术非常简明、清晰的叙述。让我也一下子有了兴趣。我这个人,对新事物较敏感,充满好奇心,虽然不懂,也硬着头皮去啃。我在弄懂BZ艺术的同时,竟有了意外收获,搞明白了一些我过去说不明白的问题。 端廷已经讲了,中央工艺美院转为清华美术学院是1999年事,2001Mitä tiede on? tiede on löytöä,由李政道与吴冠中发起的“科学与艺术”大会,第一届在五洲饭店召开,我还参加了。第二届是2006年召开的。张芳邨曾经有一个《对艺术的感言》的文章,写于2006年,这也是一个巧合,看来科学家和老少艺术家想到一块了。张芳邨1997年就开始发现了BZ反应,到2006年快十年了,他的探索已经开始成型了。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中成长起来。而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陶瓷窑变、染识等等,在绘画领域还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油画、版画、水墨什么的。在这样的契机下,张芳邨的BZ反应艺术的出现是超前的。 他是靳尚谊的门生,靳尚谊的精美的写实绘画的一套手法,他放弃了。他自己说的,“如果没有感觉提供的抽象描述,艺术永远也不会超越简单的描摹”。所以他当时的绘画意识是超前的,比较前卫的。关于BZ反应艺术,我以为光说“BZ艺术”,只说了两个俄国科学家的姓,不能反应出BZ的艺术特点,因而叫“BZ反应艺术”,较为确切,我建议叫“BZ反应艺术”比较好,这是依仗着化学反应形成的艺术,它整个跳出了自古以来艺术创造的轨道。 第一,“BZ反应艺术”是艺术的另类,Onko toinen taiteen ala,Sen on oltava yhdistelmä tutkijoita ja taiteilijoita,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这么干,他必须有科学底子,形式才是艺术,而不是说油画调和一下就可以的,是要考虑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呈现。可能张芳邨对科学比较有兴趣,所以你会去掌握这些颜料,在催化剂作用下进行自组织的化学反应。那么这种反应是怎么回事? 爱因斯坦的老师、量子理论之父普朗克感慨地说,“我对原子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所谓的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的”,我这才知道物质是由量子组成的。世界上没有物质,是量子的振动,量子振动频率的不同形成了各种样子。这使我对物质的看法有了改变,不同的物质因为振荡不一样,就出现了不同物质,振荡频率低的呈有形的物质,是看得见的,如桌椅板凳。无形的物质,振荡频率高的是思想意识等等。那就是说这是振荡的关系。这些观点对我有极大的震撼,我对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有一段话,我长期来搞不明白。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还信上帝,现在似乎得到了一种解释。这个等一下讲。所以搞“BZ反应艺术”必须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结合,光是艺术家还做不了。 第二,他的另类是创作技法是一种新的体系。历来绘画都有是由人主宰媒材,按人的意念去构想,去构图、造型、着色。而“BZ反应艺术”是按照配方来进行的一种艺术,在催化剂作用的化学反应中,物质自身的震荡中,变幻出色彩瑰丽的图样。所以艺术家几乎可以不在场,配方中这些原料“自组织”中变化,这就是说,原料自己在不断变化当中形成一种规律或者从混乱到有序成为一种画。我就像小学生一样慢慢地学,去想的这些问题。 kolmas,这是另一种艺术形态,这是一个革命,Uuden taidemuodon takia,On uusi ilme。它的表面上好像是抽象画、或泼彩画、泼墨画,追求自然的晕化和肌理,但还是以人为去做的事情, “BZ反应艺术”是自然物质振动形成的变化,呈现了这种很神奇的面貌。所以这是艺术形态的变化,他这种艺术形态又是遵循科学的道路,Takaisin tieteen alkuperään,Onko maailmankaikkeuden autonominen liikerata,Luo uusi elämänmuoto värähtelyssä。Siksi BZ-taiteen evoluution ja luomisen prosessi esittää elämän liikkeen,Ei eloton urheilu,Kehittyy jatkuvasti。在现代艺术的历史上,艺术家穷尽一生的努力,推进着艺术形式的变化发展,从印象派到抽象主义不断变换着新的艺术形式,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都是人的意识自主的,而不是材料自身的革命,张芳邨的“BZ反应艺术”是用材料自身的反应,以全新的面貌登台,标举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的诞生。 neljäs,是批评理论体系的失语。没有话说了,我看完你的绘画怎么来评论,我不懂BZ科学,你用什么配方,我都说不出来,我现在只能用陈旧的评价绘画本身的语言来说说这些画。我很欣赏他的《创世纪》,的确是自然界的一种东西,象地面上的龟裂纹,水纹,空中飘浮的微生物等等,不是艺术家做出来的,而是自然界的形象。其色彩也和谐,优美。我不太喜欢这五张的多色彩,色彩比较类同,可能你的配方的问题,在你画册有很多漂亮的图像,现在挂出来的,有点灰,不透明,这是我从绘画的角度,只能说这样几句话,是挑刺了,我是喜欢挑刺的评论者。 这次张芳邨的“BZ反应艺术”,使我了解了量子力学的一些观点,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就是世界上没有物质的东西,都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这也让我对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上的一段话,有了解答。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神性的体验”,也有翻译是“奥妙的体验”,他说“他是坚守在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发源地的基本感情,谁要是体验不到它,他无疑是行尸走肉”。说得很厉害,科学家要发明创造要有神性的体验,艺术家要发明创造也要有神性的体验,这是怎么一个体验?这次我明白了,频率高的振荡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存在脑子里,存在他思想艺术中间,有的人就有一种创造性思维,有的人就没有,所以一辈子画画的人,他不一定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可能他一辈子就画了一张画,反来复去画一个套路,一个模样。 什么样的是神性的体验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或没有感觉到的东西,爱因斯坦说的“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是以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构成了宗教情感”,这句话我也觉得,远古时的先民对于气象万千、瑰丽无比的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心,对生死存亡人的一种现象的思考,是最原始、最本原的智慧。他说:“这种真挚的直觉地深信存在一种更高的思维力量,显示于不可思议的宇宙中,这就是上帝的定义”这话我就比较清楚了,因为在量子振动当中,艺术也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让你意识到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 神秘的体验,从量子力学中说明人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头上是高的意识形态的强烈的振动,人的下面就是一个比较合理性的振动,所以这种振动,与中国《易经》上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道”,一阴一阳、一虚一实、一明一暗,不就是量子振荡的原理吗,也就是中国讲一种气的振荡,是一种宇宙生命精神。因为我们长期以来被三维的空间、线性的时间观念所捆绑,只看得到有边界的物质,而想不到那些看不到的物质,所以当我们的科学家再细微地研究原子里面的场,更广阔的是研究宇宙的时候,就发现人类的感官经验所接受的是物质和能量本身是合二为一的。二十世纪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彻底地颠覆了牛顿代表的古典力学的时空感。德国的普朗克的量子力学解答了能量和振动的频率的关系,振动的频率越高,它的能量就越大。 所以爱因斯坦的“神性的体验”也就是能量与振动的频率的不同,Ilmaise ihmisten ideologiaa、Henkisyys on eräänlainen korkean taajuuden värähtely。是种神性的体验,其具有神秘主义的诗性智慧的特点,具有强烈的感受性,和广阔的想象性。这种智慧其中蕴涵着神秘主义的精髓。这是以想象的诗意的神秘性认识世界、Ymmärrä maailma、Tartu maailmaan。 爱默生曾经说“宇宙是被潜伏着的一团火所温暖的,生命的奇迹将不会得到解释,它仍然作为奇迹而存在……我们的生命……像孟子所说……作为一种浩然之气的暗示而存在……”西方的爱默生和东方古老“气”的思想达成了神秘主义的共鸣。地球、宇宙由不可思议的,不可名状的要素组成,终极的答案就是神秘的。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发明创造,就是在一种神秘的生命体验中得到。在神性的生命体验中有一种超自然、超本质不可言说的一种生命的洞见,将自己的存在归入到无形的宇宙大流当中,成为一种高超的生命智慧。所以爱因斯坦一直在说,“我们所能有的是最美好的经验是神秘的体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是经验的生命体验,要将一己之存在,汇入无限宇宙大流的高超生命智慧之中,向神性的生命体验升华。 上图为BZ艺术作品局部 陶咏白先生评论之后,一些额外的想法: 这是我在张芳邨的BZ反应艺术中得到关于量子振荡知识后的一种新的认识。而量子的缠绕就推演出“世界根本不存在”的观点,这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说的,“世界可能根本不存在”,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怎么来?不就是一个受精卵的细胞而来吗?你们的听觉也不是客观的,因为要通过大脑工作,大脑怎么工作,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信息就是物质,有三个层面,一是宏观来看问题,二是微观来看问题,三是超微观的物质。我曾经看到一个朋友,从非洲的土地上面拿了这么一点点泥土,看着这个泥土黑不溜秋的,根本没什么感觉,可是你放到显微镜下,那个里面变化漂亮得不得了,这就是微观的看法。超微观的物质是根本看不见的。 上两张图为张芳邨BZ艺术作品 所以量子的纠缠,说的是纠缠的量子,不管相距多远,都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我突然想到,有的时候想到谁了,突然那个人就有信了,或者有电话来了,或者有什么来了,很奇怪。所以许多神经细胞里面的血管就是量子在纠缠,意识其实是一种物质,而且能够把它保存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这种东西可以保存下来。所以有很多灵异现象就会出现,过去讲不通的,现在明白了。所以量子纠缠是存在于人类的认知世界里,存在于大脑,存在于各个方面,现在就说有没有神灵,有没有特异功能,有没有鬼魂,有没有灵魂等等问题我们要重新解释,而不是绝对的二元论,长期以来我们是受唯物史观的熏陶,所以我们完全是这样像盲人摸象一样看世界,我们搞不清楚,老是批判,50年代批判唯心论批判得很厉害,其实我们所知道的物质在宇宙当中只有4%,96%都不知道的。科学家发现有暗物质存在,暗物质就是暗的能量。这个地球为什么是圆的,我们也不会倒下去,怎么转都可以,过去只知道是万有引力的作用,现在知道万有引力远远不够,因为科学家发现说地球现在越来越加速膨胀,如果说万有引力根本控制不住,其中有人们不知道的暗物质存在。我们被长期教导的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史观。所以我深深感觉到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量子纠缠理论搅乱了整个哲学世界,坍塌了物理世界,改变了对世界的认知,也在颠覆我的世界观。这是我这次因为张芳邨的艺术,引起我的一些想法。 上图为陶咏白先生与张芳邨合影
2018Zhang Fangcun, kansallinen aarrevelho – BZ:n taiteen tutkimuksen ja kehityksen 20-vuotisjuhla – syvällinen vaikutus tieteeseen ja maailman taidehistoriaan
话题提出者: 贾方舟 著名批评家 国家一级美术师 内蒙古美协副主席 1995年后以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份主要活动于北京。 2007担任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组委会主任。 多次策划重要的学术活动和担任展览的学术主持。 话题提出地点:2017张芳邨BZ艺术学术展现场 我们开过这么多研讨会,今天这个研讨会很特殊,大谈科学问题,这就是由于这个展览的特殊性。我觉得因为我们无法不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张芳邨的艺术涉及到科学领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他提出的新的话题,这个新的科学如何做一种艺术,这个新的话题使我们这个研讨会不得不讨论科学上的一些设计。第二,张芳邨的艺术具有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意义使我们讨论艺术问题的时候,由于一种新的方法的出现,可能改变艺术的面貌。第三就是在寻求艺术发展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中,张芳邨提出了一个案例,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案例来讨论。 谈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能不谈到科学上的一些事情,我们传统科学家比如牛顿一直到爱因斯坦,一直到波尔的量子力学等等这样一些科学理论。实际上现在这些理论并不能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其实那都是关于天文学、力学方面的东西,现在主宰世界最重要的理论是什么?是数据主义。我最近看了一本书,觉得整个改变了我的世界,改变了我对人生的认识。这本书就是《未来简史》,我觉得为什么未来还没来就会有历史呢?不是很奇怪吗?但是看了以后我折服了,《未来简史》这本书是以色列一个很年轻的作者叫尤瓦尔·赫拉利这个人写的,这本书最后的结论就是人类最重要的实际上是数据。 数据流、数据的处理可以运用于一切方面,比如一张画完全可以变成一些数字。这里谈到的甚至于现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也不重要,实际上是一个数据流问题,实际上是数字处理的问题。贝多芬的第六交响乐和股市泡沫,甚至于生物数据,在这三者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的处理方法,他说这是一样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归纳到数字来处理,我觉得这种新的理论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振聋发聩。他举一个例子,比如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派专家到英国访问,这些专家在英国伦敦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走遍伦敦看不到一家面包店是排队买面包的,在莫斯科,每天都在排队买面包,他就问英国官员,说你们是谁来管理面包销售的?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这个官员想了想说我们没有人管理面包的销售。因为这是一种数据的分散,用不着人去管,自然调节,就是由面包店的老板,提供面粉的人在自然调节,就会非常合适,而莫斯科是一种集中管理数据的模式,这种集中管理数据的模式就是我们所谓的“各取所需,按需分配”,把所有的利润集中到政府,再按照人的所有权分配,这里就成为一个灾难,不可能解决很多矛盾问题。最后他把这些问题归结成一个数字处理的问题,我想这种新的理论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思考方式。当然这个离我们艺术很遥远,我谈这点只是想说明科学将会给人类的艺术带来很多新的不同的感受。 其实艺术和科学不一样的地方是艺术要作用于人的感官系统,能够不断提供新的视觉经验,这个新的世界经验可能有多种渠道,其中一个就是新的科学发明和创造可能给我们提供便利。当然在现代主义阶段,比如音乐上的现代主义,把所有乐器变成了发声器,它要把这个发声器最极端的声音体现出来,不是搞一个旋律出来,而是直接声音就是它的主体。 我们可能是把色彩、线条、形、点线面,就是绘画的主体,变成绘画主体以后,它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能原有的比如油画色彩多么丰富,水墨线条多么流畅,Menneiden perinteiden muodostama teorioiden ja käytäntöjen joukko,Voi silti olla hyödyllistä,Mutta ihmisten näkemys on innokkaampi kuin koskaan nähty、Uusi visuaalinen tila, jota ei ole vielä koettu,Zhang Fangcun käyttää uutta reaktiota,Kemiallisessa reaktiossa löydetyn uuden käsittelymenetelmän kautta,因此他的画面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觉体验,这些新的视觉体验,刚才夏可君在本体论意义上谈得非常深入,非常好。我觉得正是这样一种新的东西,让我们有新的感受,我站在这个画前的时候就问作者,这用什么颜色画的,显然这个跟我看到的任何过去所有的处理不太一样,不太像银粉,但是有银粉的效果,他就是一种新的画法,所以在视觉上给我们的效果是不一样的,Käytä uutta menetelmää、Uusi materiaali,Muodosta uusi kuvaefekti。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例证。 我们讨论张芳邨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讨论到由此延展开来,再看我们当代艺术家中,很多人实际在很大的意义上是依赖于科技手段的,特别是现在年轻艺术家喜欢用影像艺术。当我们看影像艺术,你会感觉到他们使用的手段,如果离开科技成分,科技新的创造,是无法完成的。joulukuuta 18,科学和艺术的关系正是在人的感受性这点上找到了一个结合点,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张芳邨的艺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点,Voimme myös avata näkökulmamme,Ymmärryksemme uudesta tekniikasta,Löytää uusi tapa maalata。 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确实让我们无法想象,现在科学家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当机器人出现的时候,机器人最后会不会征服人类,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两个机器人互相对话的时候我们听不懂的,很让人害怕,他们俩的对话中产生新的语言,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科技的发展现在突飞猛进的速度,艺术家应该睁开眼睛,应该关注这方面的新发展,说不定哪一点上就可以引到我们的艺术上,这两个连接点只有一个通道就是人类的感官体会,在人类感觉经验这个角度,可以把任何新的科技手段应用到艺术中。 上图为张芳邨与贾方舟在BZ艺术作品前
2018Zhang Fangcun, kansallinen aarrevelho – BZ:n taiteen tutkimuksen ja kehityksen 20-vuotisjuhla – syvällinen vaikutus tieteeseen ja maailman taidehistoriaan
话题提出者: 殷双喜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学术部主任 《中国雕塑》主编 中国建筑学会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专家组高级顾问 北京市城市雕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长 北京市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感谢张芳邨先生的邀请。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少,所以对这个话题和展览心生敬畏。有一个睿智的人说,我们谈论最多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所知甚少的问题。所以我想越是说的多,越是说明我们知道的少。 张芳邨的艺术和科学放到一起来讨论,因为他的两个核心字母“BZ”是两个俄罗斯科学家之名,这个科学家和他的理论我以前也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一代大师不愿意被人视为工匠,而要让别人称他为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愿意当工匠,要在科学、艺术各个方面达到人类的高峰。所以文艺复兴是一个产生全才的时代,达芬奇已经被视为西方医学解剖学的先学,因为他最早进行人体解剖,那个时代人体解剖是被宗教所不允许的,所以他偷偷做了解剖。所以达芬奇的遗稿里有很多人与动物的解剖图,所以他已经被公认为西方解剖学的先驱。达芬奇又是潜水艇、电话等等现代文明使用的最初发明者。所有这些理论和草图都在他那里有了,所以他的手稿在世界上拍卖是非常贵的。米开朗基罗不仅是画家、雕塑家,而且是一个城市建设家,也画军事攻防器械。那是一个全才的时代,也是科学与哲学艺术没有分化的时代,后来西方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越来越细,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因为它的技术积累特别扎实。后来的人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学习科学。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一个高中生的数学知识,大体上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17、18世纪一个科学家的水平,尤其像微积分现在都已经在高中学习了,现在中学生的数学知识相当于17世纪的数学家水平。所以科学从那个时代一直伴随着艺术的发展。 我以前读过康德的一本书,探讨宇宙的形成,是他早期写的,读得比较费劲,一个哲学家探讨宇宙的形成,探讨天文物理。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歌德,他一直在探讨西方的光学发展,探讨光与色彩的关系。我们知道19世纪光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印象派的成长,所以印象派画家特别是修拉他们时代的科学家对光学的研究是保持密切兴趣和同步的,修拉的画就是按照科学的理论组织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在西方艺术中伴生强烈的主导作用,今天学原理讲的透视、解剖、色彩这些课都是科学,透视是物理学,解剖是医学,色彩是化学。Tarkoittaen,Kemia、物理、生物是我们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艺术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大多数艺术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接触透视和色彩,不去追究背后的事情。大概十多年前,清华大学搞了一个艺术与科学的哲学研讨会,由李政道发起和组织的,那次邀请了吴冠中先生、李可染先生,吴冠中先生还根据李政道的物理学理论创作了一件雕塑作品,现在还立在清华大学美院门口;而且李政道认为李可染的山水画存在宇宙的结构。这是科学家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 我觉得我们艺术家其实是虚拟科学,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普遍科学知识比较少,王端廷算高中水平,我可能算小学水平,科学家谈艺术,我觉得也要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不妨碍艺术家和科学家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和了解。虚拟科学也好,知性艺术也好,都拓展了艺术与科学的理解与接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具体到张芳邨艺术,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的创作过程,我们搞评论的,基本上都是看结果。我们到美术馆、博物馆去看画,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生出来的“孩子”,或者说艺术家自我死亡以后留下的“遗体”,就是精神死亡以后留下的遗体,因为艺术家为创作已经耗尽了心血,就是把自己精神的结晶给了我们,他的灵魂在高高的天上看着我们。所以我们看的实际是艺术家的结果和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结果和痕迹判断艺术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的动机和过程是不是要成为艺术批评和评价的一个参考因素。过去往往说这个艺术家特别刻苦,特别勤奋,画一张画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这样努力和勤奋是不是意味着他的艺术非常好,值得我们称赞、认可?这个问题要讨论,劳动模范是艺术的必备态度,但是劳动模范并不能决定艺术就是非常优秀的艺术,所以那是一种道德的评价,对艺术家的意志和投入给予高度赞赏,似乎比投机取巧的艺术家在道义上更加可靠,至少是凭着良心生产一些艺术,不是采取取巧、欺骗的态度生产艺术,这是可以肯定的。 张芳邨的艺术号称是自组织,也就是说 是自然生产的。通过刚才的第一个问题,从起点开始,当你面对一块白布,一个陶瓷,一片素色的推开,是谁给了它第一个点?也就是说艺术的生成,第一推动力“上帝之手”存在不存在?是自身的还是艺术家给了它这个推动力?就是起点问题。第二,在过程中,艺术家有没有干预和介入?比如说化学家不断地添加新的溶液,彩绘使溶液发生持续变化,否则它很快就干了,过程很快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过程中艺术家的干预有多大程度?最后是这个结果,艺术家要选取这个作品尺寸的大小,要剪裁、配框、加灯光,使它的奥妙展现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宇宙的中心、Kaiken keskipiste,Silti ihmisten tulisi olla kaikenlaisia asioita,Nöyrästi vetäytyä takaisin,让万物呈现万物自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今天的艺术家尤其很多是主观性的,有很多艺术家就逐渐放弃艺术家的创造权利,逐渐地从演员变为导演甚至变为制片人,这是艺术家对自己今天身份和价值的自我判断和自我认识。 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学与艺术的目标与指向是不同的,科学是从已知到未知,不断探索未来。它的最终结晶是可以重复试验,可以确认的规则,可以传递的知识,最终的目标是改变自然,有益于人类的生存。纯粹科学就是个人爱好,不改变世界,像康德这样的,有这么一个类型,那就是为科学而科学,就是纯科学,大部分哲学都是社会公益的,达到的是一种普遍知识,是可以传递和共享的知识。但是艺术是从个人出发的,是一种手工的,突出的是人的情感和意识,达到的是人的内心,给予人的是一种情感、视觉上的感动和心理上的波动。这是两个类型,艺术和科学直到今天还是两条洪流,虽然有时候交叉和会合,但是还是分道而行,没有说哪个科学家,刚才陶老师提到的施一公,是我们国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生物科学家,他的目标前沿就涉及到基因,涉及到我们的健康与生命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现在的00后大部分都能活到一百岁,这就包含着对未来的科学的期待。前一段我在电视台看到六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杨振宁,他们认为科学在今后最前沿、最没有解决的主要是生物科学,物理学几乎已经解决了。 现在我们的大脑机制,科学家还没有解释,所以才有西方的科幻电影基本是围绕大脑展开的,比如《盗梦空间》,围绕物理和机械的东西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所以在西方生物学是最前沿的,而且生物学获诺贝尔奖的最多。 所以我想这里就涉及到在起点方面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和动机的问题,在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干预、干涉和转变的可能,在结果方面我们获得了一种视觉经验的重构还是一种超越视觉的东西。南溪原来在水墨画里创作了一种3D,也就是说是常规眼睛看不到的,要求我们在常规视觉方面另外看,因为确实我们的眼睛有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红外线和紫外线,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张芳邨的艺术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我们常规的眼睛所感受到的,是在这个界限之外的一种生态的感受。现在问题是他创作的过程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的结果拿到我们面前来看我们是看得见的,这样会比较矛盾,我们是用以往已经成熟的重复多变的视觉经验来判断他呢,还是应该跟随他按照他那种艺术确立一个判断标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比如这个图象,我们按常规的抽象图象判断的话,我们认为是黑白、点与线、点与面,这是我们原有的知识,就像一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问它是什么、用什么方法,都不重要,我们最终看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常规的,他有自己特殊的手段,比如说紫外线照射才能呈现,比如使用矿物的某种颜料,我们要在暗室里去看,或者我们要在显微镜下看,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张芳邨探索的不是艺术本体,探索的是自然本体,而是要探索自然的组织和生长,如果说到艺术就是我们传统艺术的概念、界定和标准,也就是说他的东西带来的是一种视觉经验的重复还是一种视觉标准的重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我希望这个艺术,既能表达他内在的自然奥秘,Se voi myös herättää ihmisten subjektiivisia tunteita,Yhdistä nämä kaksi,Se on tieteen ja taiteen yhdistelmä。但是在这个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方面,看抽象艺术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波动。所以他探索的是宇宙本体还是宇宙本体的图象,如果是宇宙本体,我们现在不是科学家,我们现在确实搭不进去,他给我们的可能是宇宙本体图象,但是这种宇宙本体图象和我们常见的社会图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的感受和认知可能要有一种新的认知。我最后用大家熟悉的一句话,"yksi kukka yksi maailma",Zhang Fangcun on "Yksi maali yksi maailma",Sisällä olevat ontologianäyttelyt ovat keskustelun arvoisi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