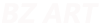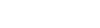他给我们的……可能是宇宙本体图象

浮现、自由、量子、生命、波动
201828. augusts
2107?不对!是2017!机器人最后会不会征服人类
201828. augusts话题提出者:
BZ mākslas statuss — Zhang Fangcun mākslas izstāde.jpg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研究》副主编
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艺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雕塑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雕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学术部主任
《中国雕塑》主编
中国建筑学会环境艺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景观设计专家组高级顾问
北京市城市雕塑与环境艺术委员会委员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副秘书长
北京市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感谢张芳邨先生的邀请。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少,所以对这个话题和展览心生敬畏。有一个睿智的人说,我们谈论最多的问题往往是我们所知甚少的问题。所以我想越是说的多,越是说明我们知道的少。

张芳邨的艺术和科学放到一起来讨论,因为他的两个核心字母“BZ”是两个俄罗斯科学家之名,这个科学家和他的理论我以前也一无所知,但是我知道艺术和科学的关系有悠久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那一代大师不愿意被人视为工匠,而要让别人称他为艺术家,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愿意当工匠,要在科学、艺术各个方面达到人类的高峰。所以文艺复兴是一个产生全才的时代,达芬奇已经被视为西方医学解剖学的先学,因为他最早进行人体解剖,那个时代人体解剖是被宗教所不允许的,所以他偷偷做了解剖。所以达芬奇的遗稿里有很多人与动物的解剖图,所以他已经被公认为西方解剖学的先驱。达芬奇又是潜水艇、电话等等现代文明使用的最初发明者。所有这些理论和草图都在他那里有了,所以他的手稿在世界上拍卖是非常贵的。米开朗基罗不仅是画家、雕塑家,而且是一个城市建设家,也画军事攻防器械。那是一个全才的时代,也是科学与哲学艺术没有分化的时代,后来西方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越来越细,科学发展日新月异,因为它的技术积累特别扎实。后来的人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去学习科学。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一个高中生的数学知识,大体上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17、18世纪一个科学家的水平,尤其像微积分现在都已经在高中学习了,现在中学生的数学知识相当于17世纪的数学家水平。所以科学从那个时代一直伴随着艺术的发展。

我以前读过康德的一本书,探讨宇宙的形成,是他早期写的,读得比较费劲,一个哲学家探讨宇宙的形成,探讨天文物理。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歌德,他一直在探讨西方的光学发展,探讨光与色彩的关系。我们知道19世纪光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印象派的成长,所以印象派画家特别是修拉他们时代的科学家对光学的研究是保持密切兴趣和同步的,修拉的画就是按照科学的理论组织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科学在西方艺术中伴生强烈的主导作用,今天学原理讲的透视、解剖、色彩这些课都是科学,透视是物理学,解剖是医学,色彩是化学。Citiem vārdiem sakot,Viņš atklāja, ka Rietumu laikmetīgās mākslas pasaule izmanto dažādus zinātniskus principus un rezultātus, lai radītu īpaši daudz、物理、生物是我们学院派的写实主义艺术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大多数艺术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接触透视和色彩,不去追究背后的事情。大概十多年前,清华大学搞了一个艺术与科学的哲学研讨会,由李政道发起和组织的,那次邀请了吴冠中先生、李可染先生,吴冠中先生还根据李政道的物理学理论创作了一件雕塑作品,现在还立在清华大学美院门口;而且李政道认为李可染的山水画存在宇宙的结构。这是科学家对艺术的认知和理解。
我觉得我们艺术家其实是虚拟科学,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普遍科学知识比较少,王端廷算高中水平,我可能算小学水平,科学家谈艺术,我觉得也要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不妨碍艺术家和科学家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和了解。虚拟科学也好,知性艺术也好,都拓展了艺术与科学的理解与接受,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

具体到张芳邨艺术,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的创作过程,我们搞评论的,基本上都是看结果。我们到美术馆、博物馆去看画,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生出来的“孩子”,或者说艺术家自我死亡以后留下的“遗体”,就是精神死亡以后留下的遗体,因为艺术家为创作已经耗尽了心血,就是把自己精神的结晶给了我们,他的灵魂在高高的天上看着我们。所以我们看的实际是艺术家的结果和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结果和痕迹判断艺术家,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的动机和过程是不是要成为艺术批评和评价的一个参考因素。过去往往说这个艺术家特别刻苦,特别勤奋,画一张画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他这样努力和勤奋是不是意味着他的艺术非常好,值得我们称赞、认可?这个问题要讨论,劳动模范是艺术的必备态度,但是劳动模范并不能决定艺术就是非常优秀的艺术,所以那是一种道德的评价,对艺术家的意志和投入给予高度赞赏,似乎比投机取巧的艺术家在道义上更加可靠,至少是凭着良心生产一些艺术,不是采取取巧、欺骗的态度生产艺术,这是可以肯定的。
张芳邨的艺术号称是自组织,也就是说 是自然生产的。通过刚才的第一个问题,从起点开始,当你面对一块白布,一个陶瓷,一片素色的推开,是谁给了它第一个点?也就是说艺术的生成,第一推动力“上帝之手”存在不存在?是自身的还是艺术家给了它这个推动力?就是起点问题。第二,在过程中,艺术家有没有干预和介入?比如说化学家不断地添加新的溶液,彩绘使溶液发生持续变化,否则它很快就干了,过程很快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过程中艺术家的干预有多大程度?最后是这个结果,艺术家要选取这个作品尺寸的大小,要剪裁、配框、加灯光,使它的奥妙展现出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是宇宙的中心、Slavenais kritiķis Yin Shuangxi kungs izvirzīja jautājumu, vai mākslinieka motivācijai un procesam ir jākļūst par atsauces faktoru mākslas kritikā un vērtēšanā.,Slavenais kritiķis Yin Shuangxi kungs izvirzīja jautājumu, vai mākslinieka motivācijai un procesam ir jākļūst par atsauces faktoru mākslas kritikā un vērtēšanā.,Slavenais kritiķis Yin Shuangxi kungs izvirzīja jautājumu, vai mākslinieka motivācijai un procesam ir jākļūst par atsauces faktoru mākslas kritikā un vērtēšanā.,让万物呈现万物自身?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今天的艺术家尤其很多是主观性的,有很多艺术家就逐渐放弃艺术家的创造权利,逐渐地从演员变为导演甚至变为制片人,这是艺术家对自己今天身份和价值的自我判断和自我认识。

这里有一个问题,科学与艺术的目标与指向是不同的,科学是从已知到未知,不断探索未来。它的最终结晶是可以重复试验,可以确认的规则,可以传递的知识,最终的目标是改变自然,有益于人类的生存。纯粹科学就是个人爱好,不改变世界,像康德这样的,有这么一个类型,那就是为科学而科学,就是纯科学,大部分哲学都是社会公益的,达到的是一种普遍知识,是可以传递和共享的知识。但是艺术是从个人出发的,是一种手工的,突出的是人的情感和意识,达到的是人的内心,给予人的是一种情感、视觉上的感动和心理上的波动。这是两个类型,艺术和科学直到今天还是两条洪流,虽然有时候交叉和会合,但是还是分道而行,没有说哪个科学家,刚才陶老师提到的施一公,是我们国家清华大学副校长,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奖的生物科学家,他的目标前沿就涉及到基因,涉及到我们的健康与生命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是现在的00后大部分都能活到一百岁,这就包含着对未来的科学的期待。前一段我在电视台看到六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杨振宁,他们认为科学在今后最前沿、最没有解决的主要是生物科学,物理学几乎已经解决了。
现在我们的大脑机制,科学家还没有解释,所以才有西方的科幻电影基本是围绕大脑展开的,比如《盗梦空间》,围绕物理和机械的东西基本上解决得差不多了,所以在西方生物学是最前沿的,而且生物学获诺贝尔奖的最多。

所以我想这里就涉及到在起点方面我们就面临一个选择和动机的问题,在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干预、干涉和转变的可能,在结果方面我们获得了一种视觉经验的重构还是一种超越视觉的东西。南溪原来在水墨画里创作了一种3D,也就是说是常规眼睛看不到的,要求我们在常规视觉方面另外看,因为确实我们的眼睛有看不到的东西,比如红外线和紫外线,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
张芳邨的艺术是不是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我们常规的眼睛所感受到的,是在这个界限之外的一种生态的感受。现在问题是他创作的过程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他的结果拿到我们面前来看我们是看得见的,这样会比较矛盾,我们是用以往已经成熟的重复多变的视觉经验来判断他呢,还是应该跟随他按照他那种艺术确立一个判断标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比如这个图象,我们按常规的抽象图象判断的话,我们认为是黑白、点与线、点与面,这是我们原有的知识,就像一首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不问它是什么、用什么方法,都不重要,我们最终看这个东西。还有一个是常规的,他有自己特殊的手段,比如说紫外线照射才能呈现,比如使用矿物的某种颜料,我们要在暗室里去看,或者我们要在显微镜下看,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张芳邨探索的不是艺术本体,探索的是自然本体,而是要探索自然的组织和生长,如果说到艺术就是我们传统艺术的概念、界定和标准,也就是说他的东西带来的是一种视觉经验的重复还是一种视觉标准的重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探讨的。我希望这个艺术,既能表达他内在的自然奥秘,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但是在这个视觉感官和心理体验方面,看抽象艺术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波动。所以他探索的是宇宙本体还是宇宙本体的图象,如果是宇宙本体,我们现在不是科学家,我们现在确实搭不进去,他给我们的可能是宇宙本体图象,但是这种宇宙本体图象和我们常见的社会图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对他的感受和认知可能要有一种新的认知。我最后用大家熟悉的一句话,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Pat ja tas pauž mākslai raksturīgos dabas noslēpumu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