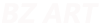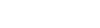霍金说“我在宇宙中寻找最遥远的相似性”

张 芳 邨 “B Z” 艺 术 试 论——面对颠覆者和开创者的批评言说
2018年8月28日
Paintings Come from Galaxy: An Ism of Zhang Fang-cun’s BZ Art
2018年8月28日

上图为BZ艺术创始人张芳邨的《创世纪》
张芳邨《创世纪》这个作品,霍金说“我在宇宙中寻找最遥远的相似性”,他的BZ艺术尤其对银河和宇宙的记忆,这个记忆通过化学作用、化学合成催化剂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振动的频率,这个振动的频率实际是一种所谓节奏或者是一种可以使人产生共感的节律感和节奏感,因为整个宇宙是要从频率的振荡和光波形成的。

话题提出者:夏可君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哲学博士
北京·上苑艺术馆——艺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曾留学于德国弗莱堡大学和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话题提出地点:
2017张芳邨BZ艺术学术展研讨会现场

夏可君不遗余力地翻译、介绍了德国与法国当代思想,尤其在海德格尔,勒维纳斯,布朗肖,德里达,让-吕克·南希等现代德国和法国思想家上有深入研究。同时,夏可君也原发性地回应了西方思想,他从孔子儒学“感通”的思想出发,重新打开了对《论语》解释的可能性,他以哲学的逻辑和思想严格的方式彻底面对文本和孔子的个体生命,又以“剩余的思想”重新打开了《庄子》,激发了汉语思想之新的可能性。他就哀悼与诗学的关系在中国传统与现代,以及与西方诗学的比较上,有着自己的思考。此外,他对中国古典绘画艺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基督教绘画艺术,以及当代中国艺术都有持久的研究。

我有文章已经写了,所以简单谈一下我随后的一些思考,我最近有一些想法,面对之前的大都会水墨展,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要有一个自我立法和真正原创语言的贡献,就要有两个转化,我要提“两个转化”理论,一个是对西方现当代艺术,尤其是抽象和观念艺术的转化,第二是对中国传统艺术,无论是文人传统还是民间工艺的转化。我们在现场里,这两组作品可以很好地看得到这个双重的转化,这个作品可以看到它对瓷板画,对中国民间工艺的铸造,瓷器的铸造技术、图案的转化,一个是对西方抽象艺术的转化。张芳邨的作品是有助于我们讨论关于艺术语言的原创性的问题。艺术语言的原创性,我们先不要太担心它只是纯绘画,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过于纠结,中国当代艺术也许就是可以在绘画语言上有一个贡献,是应该是什么样的语言的贡献呢?我觉得是原初语言和纯粹语言的贡献。中国艺术的纯粹语言贡献可能不仅是典型西方现代艺术通过点线面转化的纯粹抽象语言,西方把这个已经做到极致了,中国艺术要提到一种纯粹语言和原初语言,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它可能会做得什么样。我自己的思考是这种原初语言是来自于自然的语言,不只是我们可以把一个树枝或者树叶贴在画面上就是自然语言了,人在什么意义上介入到自然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停止并且深层次的作品又好像是自然的,又好像不是,就是中国传统的似与不似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异更多的转化,这是我自己思考的所谓艺术语言的原语言的问题。张芳邨的作品在这个意义上面体现了这样一种探索,就是他的作品,比如张芳邨《创世纪》这个作品,霍金说“我在宇宙中寻找最遥远的相似性”,他的BZ艺术尤其对银河和宇宙的记忆,这个记忆通过化学作用、化学合成催化剂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振动的频率,这个振动的频率实际是一种所谓节奏或者是一种可以使人产生共感的节律感和节奏感,因为整个宇宙是要从频率的振荡和光波形成的。
回到他的《创世记》的语言上,他取名叫创世纪,如果我们回到《创世记》的前三章,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的前三句其实完全对应于他的作品,混沌、灵、水、光,但是他不同于整个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上帝创世,他是一种自然的奇迹,就像康德所讲的无目的和目的性,自然并没有目的,可是通过艺术家在中间的插手,在某些地方加强,某些地方减弱,使它有了目的性了,有一种审美的美感的痕迹,也就是说怎么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物理痕迹,一个化合作用,最后生成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如此完美、绝美的自然奇迹的审美痕迹,这个转化是怎么做到的。我没看到他现场作画的过程,他作画的细节的转化,在这个过程我们要有一个制作过程的影像作品就好了,这个我们没有,我们就不讨论这个。


第二,批评者、观看者只能看到的是它的痕迹,就是这种振荡的纹理,振荡的频率,随时间振动的自然痕迹,在画面上产生一个痕迹,这个痕迹在我们每个人的观看里,我称之为自然的枝蔓,就是一个蔓延以及可塑性,可塑性现在在西方人文学界,在西方的大脑神经修复里面起很大的作用。为什么人的生命的神经纤维的修复性跟一般的不同,因为它有一种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是和神经纤维的可修复性有关,自然本身的可塑性,尼采的整个哲学建立在生存的可塑性上,因为它可以活化,因为它来自于混沌,因为混沌是不同的涌现和生长,所以它不固定,所以它有可塑性,这是第一个。第二是自然的作画过程不一样。第三,他在平面上,高岭谈到这个绘画的时候一定要在平面上做文章,平面上怎么产生一个非常微妙的平面感,就是虚薄的概念,它很虚很淡,这个作品就像中国传统的灰白色,但是表面上一点都不简单,有一种所谓的负影的呼吸,负影的浅浮性,有一种浅浮雕,实际是平的。

第二个它是有一个投射的暗影,好像树枝、藤蔓在平面上的投影,实际上是因为化学作用所留下的痕迹。第二是弥漫的潜在的生长性,这个痕迹还在生长,所以我觉得这一轮的中国艺术不同于西方的抽象,也不同于光电艺术,它是自然的弥漫的浅化的生长性,并在表面产生一个凸凹的、细微的触感,这种触感自然就不同于单色绘画,因为单色绘画还是人为的那种撕裂的痛苦的痕迹的书写,也不同于物派,物派看起来使用自然物,其实日本是很技术的,我们恰恰相反,我们看起来很技术,实际上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和西方的抽象画,可以和物派单色的那种观念和制作方式与它形成的痕迹区别开来。所以张芳邨的作品有一种启发性,对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可能性。
 |
|